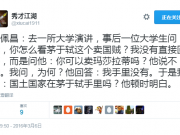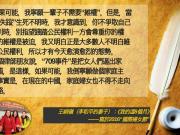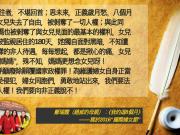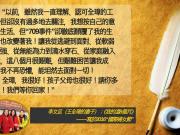敬告读者
为更有效地使用资源,《中国人权双周刊》从第181期起并入中国人权主网页。网址是:http://www.hrichina.org/chs。我们将继续遵照本刊宗旨和编辑方针,一如既往地为读者服务。
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从废除死刑讨论来看公共理性的培育
前一阵,因药家鑫案,网络上重新燃起了废除死刑的争论。虽然立法层面的法条修改与司法实践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对药家鑫案我们期待的是严格执行现行法律,而废除死刑需要遵循立法程序,不过这两者并不对立。此次倡导废除死刑者还是很好地借用了这个话题,激发了公众对有关死刑的讨论热情。
从参与角度来说,发言者很多,用语比较激烈,说明该讨论成功。然而从说理方式上看,该讨论体现了多少公共理性精神呢?我所说的公共理性是指就公共话题讨论体现出来的理性精神,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讲道理的程度,及公民平等参与的姿态。
1949年以来,公共话语空间因为权力高度垄断,而被极度压扁,学校教育灌输的亦是不容质疑的独断话语,阶级斗争话语方式的余毒延续至今,难以清除。人们都不知道怎样讲道理了。但随着互联网兴起,给公共空间的成长带来了希望。网络常常出现热门话题,就说明民众对公共事件有强烈的关怀。不过公共关怀与公共理性还不是一回事,我们需要关怀,但需要的是有理性的关怀。在这场讨论中,力主废除死刑的滕彪、熊培云等人遭到了许多过激“关怀”,甚至受到谩骂与人身攻击,这就全然违反公共理性。
废除死刑是一个培养公共理性很好的话题。首先大家都有话可说,我们既受朴素的传统民间思想“杀人偿命”的强大影响,也受到宽容、不以暴制暴等现代文明观念的冲击,因此有关废除死刑的命题从起始就有明显的争议性。任何公共权威的形成,只有通过公共理性的检验,才能获得合法性,形成规范性力量。作一点理想化的展望,我们可以不断地通过类似死刑话题的充分讨论,达成公众共识,进而促进制度的某些变革,同时也带动民众更深层次的理念思考。好在死刑还未列入敏感话题,大家发言可以少些顾忌,讲出心里话。更重要的是,有关死刑牵涉到多方面问题,可以培养公众的理性思考。
从这次废除死刑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中国社会中,公共理性极度缺失。比如,周杰在《死刑存废与公共抉择》一文里抬出列宁、毛泽东等专政大王的“正统”言论作为立论依据,反驳者就无法说话了。况且,周杰还有更骇人之言:列宁、毛泽东“冷酷残忍的面孔背后不正包含着他们对中国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众最深沉、最真切的仁慈和关爱么?大残忍背后必有大仁慈”,以“政治家的眼光和谋略”,死刑关乎国家建构。如此,死刑讨论成了政治问题,反对死刑者似有颠覆国家政权的图谋;占据了如此政治高点,草民自然就不敢反驳了。周杰所言实际上是强权性话语,违法公共理性。
还有一些人认为,主张废除死刑者打着理想主义的旗号,实际上是为丧尽天良的残忍凶手辩护。这种臆想是典型的诛心论。1949年以来,我们受此类简单的思维方式的苦太多了,从反右到文革,民众早该告别这种反理性的诛心论了。退一步讲,即使有人出于利益关系为药家鑫辩护,但只要言之成理,遵守言说的基本规则与逻辑,也应允许,言者无罪。
常见的支持死刑论还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说。道德义愤诚然有合理性,应该受到尊重,但义愤仍需要理性来分辨明示。道德谴责是需要的,但于公共社会仍需要遵循理性精神,这是建设公共社会之必需。但群情激愤蔓延为语言暴力,则是对公共社会的破坏。应该看到在中国公共社会中充斥语言暴力,这是党文化所致。
药家鑫一案,凶手残忍恶劣,理应受到法律的公正审判,这不用多说。但是,网上出现的文革、群众运动式的言语暴力也是值得警惕和反省的。比如北大教授孔庆东在此次讨论中,斥药家鑫:“他长的是典型的杀人犯的那种面孔”,“这是一个杀人犯的气质”,并加上“满门抄斩”,“断子绝孙”等狠话。这种谩骂、贴标签、诅咒式的语言暴力,不仅破坏了理性讨论,而且有害于公共社会,反理性,助长社会的仇恨、暴力。药家鑫诚然残忍,但是社会与民心需要向文明方向发展,因此面对犯罪和凶犯,我们也需要持守理性,坚持普世的人权原则,对罪犯严格执法,但尊重其权利和人格。由此,社会和民心的道德才会提升,而不是因罪犯而下降。
作为该讨论的另一方,学者萧瀚主张废除死刑,因而招致到谩骂和诅咒。为此,他反击反对废除死刑者为“嗜血者”,这也属于独断性话语,将对方符号化。如果我们多些同情式理解的话,许多人激烈反对废除死刑,其背后实是对中国司法不满、不信任。因为在中国,司法被权力随意操纵,法律公正完全无保障。民众之所以对李刚案、药家鑫案、钱云会案等等有如此大的反弹,就在于民众对司法不公、权大于法感到愤怒。药家鑫案所体现的群情激愤,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着权力操纵司法。
在有关药家鑫案的讨论中,有些人主张对药家鑫宽容。虽然中国社会的宽容意识很欠缺,需要多加倡导,但在正义非常脆弱的情境下,一味强调宽容则是纵恶,而宽容也沦为廉价品。因此,在正义无保障的状况下,过分宣扬宽容自然会引起公众的反感,乃至被怀疑是为强权者帮闲。对药家鑫宽容了,那对于受害者张妙一家难道不是残酷吗?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被视为体现宽容的典范,但近年来该委员会也受到一些质疑,很多和解有“被和解”之嫌,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巨大伤痛终生无法愈合。还有历史上,中国的强权者一向是残忍地铲除异己,对于他们我们该宽容吗?面对他们的残酷,公正又该如何体现?
总之,基于常识的质疑是有意义的,永远值得我们审视与思考。对药家鑫案的群情激愤,实际上是民众对司法不公的抗议,及对司法公正的呼吁。当今,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权力至上,公正无保障。不过,如果我们仅停留于对不公正的抱怨,则于事无补。中国需要社会大环境的改变,而增长公共理性的精神,正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道路之一。理性精神才是实现社会宽容的保证,也就是说在公正的原则下,经由理性审视,才能有真正的宽容;否则就是情感的滥用。
在公共事务中,公众秉承着平等、相互尊重、理解的态度来参与,这就可以促进公共理性的增长。我们需要警惕专断言语,避免非黑即白的简单化思维方式。公民之间的讨论,既不需要臣民式的上书谏言,也不需要代表人民与正义、居高临下地审判,更不能实行语言暴力——诛心、谩骂、诅咒等等。我们应坚持普世价值,公正、理性、宽容、非暴力、尊重生命等等。我们所说的公共理性,就是为了建设这样的社会。如果我们的国家以公共理性来支撑,普世价值就可以在中国实现。
2011-05-09
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1025
关于我们
本刊将秉持理性、平实的方针,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民众的维权活动,对社会焦点问题进行分析评论;同时普及宣扬人权理念,系统介绍国际人权法律知识和维权案例,推动法制建设,扩大公民社会的空间,为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服务。
过往各期
六四专题
搜索
热门转载

-
时事大家谈:赞“一士之谔”,中纪委反击中宣部?
-
小品:讨伐任大炮
-
魏京生: 任志強很勇 如同自己當年
-
任志强: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式分析
-
微自由: 任志强微博被封
-
《大炮有约》01 尼玛开撸,戴上头套谁敢惹咱俩
-
《大炮有约》任志强:不怕向任何人开炮
-
【中国情报】肃清微博大V | 中国走向法西斯二次文革? 20160301
-
批习「媒体姓党」遭清算 任志强微博被封 学者:已到二次文革边缘
-
党媒批任志强暴露党群对立

-
国土国家在茅于轼手里吗?
-
12国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
-
12国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
-
12国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