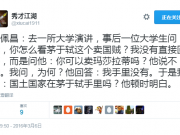敬告读者
为更有效地使用资源,《中国人权双周刊》从第181期起并入中国人权主网页。网址是:http://www.hrichina.org/chs。我们将继续遵照本刊宗旨和编辑方针,一如既往地为读者服务。
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公民权利手册(三十一)
(续第57期)
努力走向公民社会之五:“公民不服从”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
第二个问题:“公民不服从”运动与公民
“公民不服从”是一种违法的行为,而且公民在从事这样的行为时,等待的是惩罚。那么“公民不服从”这种违法行为的合法性基础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约翰•罗尔斯的观点是比较正确的。他的看法就是说,公民,首先是个公民,然后才能有“公民不服从”。如果法律合乎正义,那么公民应该遵守这个法律。但是法律不是必然地永远得合乎正义,某一部法律、某一个法律条款在一定时期内,有可能是偏移正义的价值的。当法律合乎正义的时候,公民有义务遵守它;那么,当法律偏离正义的时候,公民也就有理由不服从它了。这就是“公民不服从”的合法性的根源。
约翰•罗尔斯理解得非常清楚。他对于“公民不服从”的使用范围和主体资格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他认为“公民不服从”这种行为必须在一个正义接近实现的社会才可以行使。什么叫正义接近实现?就是说这个社会整个的方向是正义的方向,具体说就是一个法治的和民主的社会。法治的民主的社会它整个政治体制的设计就是朝向正义应该实现或者接近实现的目标发展,法律的最终诉求目标是正义,追求正义的实现,但是法律不一定总是自始至终朝向正义的目标,法律也可能偏离,而这个时候,公民可以“不服从”这样一种社会运动方式,使它变好。
简单地说,“公民不服从”必须建立在“公民”存在的基础之上。如果一个社会不是一个民主的和法治的社会,这个社会根本没有公民,而只有“臣民”、“老百姓”、“访民”、“暴民”和“屁民”,那么“公民不服从”则没有施行的社会基础。比如在撒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如果你行使“公民不服从”的话,结果就是一定会被活埋;在金正日统治下的北朝鲜行使“公民不服从”,结果就是一定被枪毙;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你即便服从,也有可能不被统治者认可,他们会因为你服从得不完美而给你严酷的迫害,何况不服从?对专制制度的不服从也有相关的事例,但是一般来说成效有限。
“公民不服从”,是因为有公民存在而存在,是因为公民的权利暂时被剥夺,是因为公民的权利部分被剥夺,所以才有“公民不服从”这样的改造社会的方式。在一个集权社会、专制社会下,你本来就不具备公民资格,你是一个奴才,你永远没有权利去实现正义,因为正义被“永远正确”的人所垄断,那么你也就没有权利暂时被剥夺的现象,因为你的权利被永久剥夺了;那么也不存在说你少数情况下没有保障,再去进行抗议,就不存在问题。毛泽东早就说过,不许反动分子乱说乱动,要么死亡,要么服从,你哪里有不服从的机会?
甘地在印度,马丁•路德•金在美国南方,那应该说都是一个正义接近实现的社会,是一个民主的、法治的社会。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再怎么黑暗,它也是崇尚人性自由的;黑人在美国遭受的待遇再不公正,美国的开国精神也不支持这样的不公正。所以罗尔斯把这个“公民不服从”的行为界定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下,他认为,实行“公民不服从”这种行为的人的资格,也必须是公民,他首先享有公民权利、承担公民义务,这样的人才可以实行这样的行为——“公民不服从”。
在圣雄甘地那里,“公民不服从”一开始叫做“非暴力抵抗”,后来又叫做“非暴力不合作”;在美国著名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那里,“公民不服从”叫做“消极抵抗”,后来的学界把这些概念总称为“公民不服从”。有学者认为,“公民不服从”理论是宪政理论的重要补充,它贯彻了宪政的原则和精神,赋予现代宪政理论以可操作性。宪政理论如果不以此理论作为补充,就不是彻底的行之有效的理论。据我所了解,德国甚至把“公民不服从”写入宪法条款,就是公民有权利不服从恶法,只有德国的宪法中写入这个条款。根据德国的宪法,德国公民在一定情况下,有权利不服从法律,这在普通中国人看来,恐怕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
“公民不服从”违反的是法律的文字,契合的是法律的本质,法律的本质应该是追求正义的;如果法律的文字违反了正义,我违反了法律,恰恰说明我和正义是一致的,这时候,这个违法行为有另一种价值,就是正义的价值。近代以来,“公民不服从”的理论和运动为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正是“公民不服从”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众多领袖中的最杰出代表。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等人所行的就是这个世界的正义的价值。以甘愿承受法律惩罚的方式去干预不正义的社会,这些人能不高尚吗?
“公民不服从”思想几个最有影响的根源是苏格拉底、梭罗、甘地和马丁•路德 •金,但苏格拉底是讲为什么应当服从一个不公正的法律,而后两人则是讲为什么应当不服从。苏格拉底面临死刑判决,他有很多逃脱制裁的机会,但是他选择了服从法律的判决,坦然面对死亡,而不是逃避。苏格拉底不服从雅典的法律,为雅典引进了新的神,做为一个伟大的学者,他是知道的,这样做是违反法律的,但他甘愿接受法律的惩罚,以此来矫正法律,使其接近正义。这是公民不合作的伟大样板,也是公民追求正义的伟大样板。
苏格拉底所生活的时代是古希腊民主政治昌盛的时代,抛开雅典的奴隶,只看雅典的公民,我们会发现雅典的民主政治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出色的——普选、代议制、公民政治、权力制衡,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要素在古希腊都有雏形。也就是说,雅典的民主政治是一个接近正义的民主政治,它当然不如当今的瑞典和美欧更接近正义,但是比当今的朝鲜和古巴等国还是更接近正义的。于是,苏格拉底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实施了“公民不服从”,并为此付出了最具有悲剧色彩的代价。在苏格拉底一案中,一方是追求真理、舍身取义的伟大哲人,另一方则是以民主自由为标榜、被视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这两方是“公民不服从”完美的结合。
“公民不服从”一方面需要公民正义精神以及为正义精神而舍己取义的勇气,另一方面需要一个接近正义的社会环境。当公民为了正义理想而行动的时候,在根本上也需要公民维护那些接近正义的基本秩序。苏格拉底在死刑判决后,认为自己必须遵守雅典的法律,因为他和国家之间有神圣的契约,他不能违背。这里面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苏格拉底和他的国家有神圣的契约,他在他的国家有投票权,有政治参与权,这个国家的法律在制定过程中有他神圣的一票,而且这个国家的法律明文规定:不喜欢这个国家的公民可以带着自己的财产离开这个国家。你可以说雅典千般不好,但相比那些经常剥夺公民出国权的现代流氓政权还是要好一千倍;相比那些限制公民的迁徙自由的现代流氓政权还是要好一千倍。于是,你就可以理解苏格拉底为什么用生命为代价来维护他可爱的雅典了。
在从前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当今的朝鲜和古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公民不服从”没有相应的社会基础,没有这个社会应该具有的“公民”。草民们和老百姓们不是古典意义上的公民,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他们面临的是一个非人的社会。他们没有投票权,没有政治参与权,没有社会生活的选择权,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背离正义的社会,这个社会不给他们“不服从”的一切机会,统治者要求他们的只有服从,哪怕是屈辱地服从。
人民可以全体服从统治者一个时期,也可以部分永远服从统治者,但是,如果要全体人民永远服从统治者,那是不可能的。即便最专制的制度里,也有“公民不服从”的种子在酝酿着成长,即便最保守的文化里也有“公民不服从”的精神在孕育,专制统治者想要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不可能的。即便他们不遭到法律清算,也一定要遭受精神的鞭尸。
(待续)
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1148
关于我们
本刊将秉持理性、平实的方针,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民众的维权活动,对社会焦点问题进行分析评论;同时普及宣扬人权理念,系统介绍国际人权法律知识和维权案例,推动法制建设,扩大公民社会的空间,为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服务。
过往各期
六四专题
搜索
热门转载

-
时事大家谈:赞“一士之谔”,中纪委反击中宣部?
-
小品:讨伐任大炮
-
魏京生: 任志強很勇 如同自己當年
-
任志强: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式分析
-
微自由: 任志强微博被封
-
《大炮有约》01 尼玛开撸,戴上头套谁敢惹咱俩
-
《大炮有约》任志强:不怕向任何人开炮
-
【中国情报】肃清微博大V | 中国走向法西斯二次文革? 20160301
-
批习「媒体姓党」遭清算 任志强微博被封 学者:已到二次文革边缘
-
党媒批任志强暴露党群对立

-
国土国家在茅于轼手里吗?
-
12国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
-
12国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
-
12国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