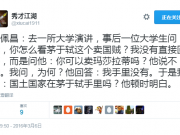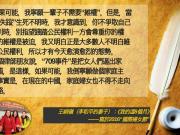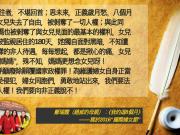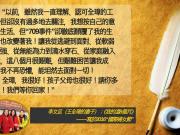敬告读者
为更有效地使用资源,《中国人权双周刊》从第181期起并入中国人权主网页。网址是:http://www.hrichina.org/chs。我们将继续遵照本刊宗旨和编辑方针,一如既往地为读者服务。
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超越“权利”的语言—中国维权运动的挑战(上)
“权利”(Rights)、“人权”(Human Rights)等概念,在全球化的今日,已普遍进入到各个国家中,甚至成了各地社会行动者最常使用的改革诉求概念。劳动权利、政治权利、环境权利、消费权利等概念,近20年来以全球为范围大行其道,对于中国,同样也是如此。在中国,社会改革团体多半被称为“维权团体”,社会改革律师被称为“维权律师”,可见“权利概念”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
然而,在倡议权利、人权的同时,我们也观察到,权利的相关概念一方面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的主流语言,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架构下,竟也造成了许多限制。我们观察到,在中国人民获得了越来越多法律保障的“权利”之后,人民的“权力”却依旧薄弱,难以对抗强大的威权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或许,对于各方的社会运动者而言,回头彻底检讨“权利”这个概念的时候到了。
难以落实的劳工权利
“权利”概念究竟有何问题?大体上来说,一方面,有着诸多的外在与内生条件问题,使得各种权利难以落实;另一方面,透过落实权利所能改变社会现实的效果,往往也有所局限。关于这种“失落的权利现象”,我主要有两个例子:
自2008年开始,为了改善中国劳工长年来受剥削的诸多问题,中国政府颁布了《劳动合同法》,同时修正或公布了诸多劳工相关法令。这一连串的法律里头,对于劳工的法定工时、最低工资、加班费、假日加班工资、资遣费等,都有了相当详细的规定,也等同于赋予了中国劳工许多工作上的法定“权利”——这些内容是雇主不可侵犯的,劳工如果受到侵犯,可以请求政府介入或上法院诉讼,最终可以讨回法律上应有的权益。举例来说,雇主如果要工人超时工作或在国定假日时来上班,却不给予他依法加倍的工资,就是违法,受害劳工可以到政府劳工局或上法院,争回这些法定“权利”。甚至,不只是法定保障的权利,如果劳工和雇主约定好雇主要提供哪些薪资或福利,这些也就成为劳雇契约上“劳方的权利”——雇主不遵守,劳方可上法院告他。
然而,我们在现实中发现,许多劳工倘若这些法定权利受损了,却也只能摸摸鼻子认栽,诸多劳工(特别是非重点大城市的劳工)根本从未真正享有这些法定劳工权利。法律上规定的加班费、资遣费、假日加倍工资等,对他们只是“纸上谈兵”,尽管法律要保障这些权利,劳工却未必享有。
现实的状况几乎是,法定权利受损的劳工有万千,但能真正争回完整权利的劳工,可能只有千百。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无它,“程序成本”太高!劳工为了确保工作无虞,避免受到雇主报复,就是权利遭到侵害,往往也只能隐忍。就是被逼得要上法院,在没有足够费用聘请律师的状况下,要怎么和各个有规模的公司缠斗,判决决果如何,仍是未定之天。最后,真能争回法定权利的劳工,当然是少之又少。
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这些法定权利真的比较能被落实了,这和“劳工被剥削的处境”被改变,仍有着根本的差距。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工因为缺乏生产工具,被迫要将自身的劳动力作为商品,贩卖给资本家以换取工资,而让自身的生产成果归资方所有。这一套将劳工视为商品的“交易关系”,可说就是劳工“受剥削”的源头。中国政府也许可以颁布诸多劳工法令,些许改善资本主义下资方赤裸裸对劳工的宰割和剥削,但却很可能无法触及这些根本的问题,甚至可能只会模糊了问题;剥削依旧,只是程度稍稍缓和罢了。但若遭遇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政府很可能又会放松劳工法令,让资方恣意剥削获利的可能恢复过来。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逻辑,也是落实各种“权利”所未能处理的问题。
沦为特权的人权:言论自由
再举一个例子。上述有关“劳工权利”无法落实的案例,是有关“私法”权利的例子。但其实不只在“私法”领域是如此,就是在“公法”领域,实际上各种法定的权利、甚至是宪法明定的基本权利,例如言论自由、集会游行自由、人身自由等,现实中究竟落实了多少,也相当值得关注。
我们一般称这种宪法层次、公法领域的权利,叫做“基本人权”,也可用“人权”、“基本权”称之。为了和前述私法领域的“权利”区别,以下我以“人权”称之。我们会发现,这些“人权”在当代中国,更容易成了口惠而实不至的“宪法口号”。
以言论自由为例。中国《宪法》明文规定,人民的言论自由应受保障。但稍具备现实认识的人都知道,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状况,仍是极度地遭受政府高压。不但起草《零八宪章》的知识分子们已沦为“颠覆政权”的政治犯,诸多维权律师、维权团体,也将遭遇政府刁难、甚至逮捕。中国人民有的言论自由,只是“不可以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只要稍稍越过那条底线,镇压和清算立即而来。
言论自由作为人权系谱中的根本,不只是保障人民有思想和沟通不受政府控管的基本权利,而且更要保障社会中边缘的弱势者同样也有公平发声的机会。但是,这份言论自由所欲追求的理想,和当前现实有着极大的落差。就是中国人民渐渐有言论自由,各种民营的出版业者或报章杂志日益有了发言的空间,但社会中弱势者的言论,却依然未获重视。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平台,能让他们的言论,等同于社会中优势者的言论一般,被公平地重视。
今日我们看到:有钱的大企业可以花钱买广告、宣传符合其利益的言论,甚至可以买下媒体;而弱势的劳工和农民,又能怎么发出他们的不平之鸣?所谓人人平等都有着言论自由,“只是写在宪法上的一句好听的空话而已”,不正是如此?!未能面对社会不平等现实根本的人权,其实只是少数人的人权。
自由主义权利观的概念
从以上我反省到,不论是“权利”还是“人权”,作为一项全盘性的社会改革论述,有着它外生与内在的局限性存在。我们有必要认清这样的问题,才能“超越权利的语言”,找寻真正能促成人民解放的改革概念。
回归问题的根本:什么是“权利”?什么是“人权”?权利哲学的研究者们指出:“权利是人民得以据此请求政府排除外在侵犯自身特定内容,或要求提供特定内容的一种资格。”权利所排除或限制的对象,既针对人(私法上的权利,例如主张财产权可排除他人占有或使用自身的财产),也针对国家(公法上的人权,例如主张言论自由可排除政府过度限制人民发表异议的法令或管制)。
从这样源自传统自由主义的权利定义来看(也是本文所采用针对权利与人权的定义),不论是权利或是人权,概念上有几个重点:
第一、权利主要是一种要求政府“排除外在侵犯”特定内容的概念(如“自由权”或“财产权”)。很少数情况才是一种要求政府“提供特定保障”的概念(如“社会权”或“劳动权”)。
第二、权利的实现与否,需要透过“人民向政府请求介入”,才能排除侵害或要求提供。
第三、权利此种资格,原则上必须由被权利保障的“个人自身”才能主张。
第四、各种权利内容都有着相应社会脉络的缘起,是要规范特定的社会秩序,以及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例如在采取自由主义权利观的社会中,权利的内容主要是在私法上保障“财产权”,促成各种商品交易和使用上的安全;在公法上保障“自由权”,避免国家过度限制人民自由。
权利概念的内在局限
这些权利的概念内容,表面上看起来并无太大的问题。依循着这样大为盛行的权利概念,不论是政府的各种施政、或是维权团体的改革倡议,这几年来不断朝向让中国人民获得更多的“权利保障”,或是有更完善规范各种权利的“法律规定”逐步地推展。前述提到的《劳动合同法》即为一适当的例子。
但这样以“权利”相关概念推行的改革措施,并非毫无阙漏。或者,至少说,在采取权利概念为改革诉求所使用的语言时,有必要思考其可能的“盲点”所在,才能让改革倡议不致限于权利概念的内在局限中。
以下是我考察权利与人权的内在概念特别所观察到的问题,至少包括五项内容:权利概念“忽视救济程序成本”、“单单指向国家与法律”、“流于个体化”、“忽略结构”、以及“成为改革的霸权语言”。下面分别进行论述。
一、忽视救济程序成本
法律也许保障了人民许多权利,但问题是,当这些权利被侵犯时,人民有没有能力保障这些权利?人民能否采取适当的行动救济被侵害的法律权利?如果没有办法,那么就是法律明定的各种权利,不论是私法上的最低工资、加班费保障、工伤补偿,或是公法上的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也都是形同一纸空文——对弱势者来说,只是写在法律上好看的规定罢了。
受侵害的人民为何会没有办法采取行动救济这些权利?原因是采取这些行动是要成本的!和侵犯者谈判、调解、仲裁、向官方检举、上法院诉讼、聘请律师等,都要花费大量的劳力时间费用,并要承担因主张权利继而招致报复的风险(不准请假出庭、遭解雇、私下遭攻击等);而且越是重要的权利被侵犯,侵犯者越有权有势,往往要花费的程序成本更高,非要上诉到底,否则没得了结。这些就是所谓“救济权利所要耗费的程序成本”。但传统权利概念的思考下,往往不会讨论到这样的程序成本的问题。政府可能规定了许多的权利应受保障,但实际上真正能担负成本、历经难关、实现权利的人,十个中只有一个。这样回头来看,保障许多权利的规定,又有什么意义呢?
尽管当代诉讼法特别重视在捍卫各种“实体权利”的同时,也要保障人民的“程序权利”——改革争讼制度,减少人民救济权利所要耗费的劳力时间费用,降低人民维权的程序成本。诸如推行调解、仲裁机制,诉讼上增设小额和简易诉讼,提供弱势者免费诉讼代理等。但是,客观来看,直到目前为止,成效仍相当有限。以权利概念推行的改革中,还是重视“实体权利”为多,关注“程序权利”为少。这也反映各种权利概念不容易关注到“究竟实际上能否容易实现”的局限所在。
二、单单指向政府与法律
前述“权利的定义”的第二项中我们提到:不论是权利或人权的实现与否,需要透过“人民向政府请求介入”,才能排除侵害或要求提供。但问题是,权利受侵害的人民未必有能力寻求政府介入,而且政府也未必会依法介入救济人民;有时政府就是有意介入,却力有未逮,拿违法侵权的人或公司没办法。相较之下,人民还不如有能力“自救”,本身就握有实现权利的“权力”,逼侵权者退让。但这却是“单单指向政府与法律”的权利概念所无法关注的方面,也是其局限来源之一。
举例来说,政府可能保障劳工诸多权利,但现实中,劳工根本无能无力请求政府介入实现被侵犯的权利,遭遇到被积欠薪资、加班费、福利等,为了继续工作或快速找到下一份工作,也只能摸摸鼻子认栽。劳工鼓起勇气找上劳工局,也可能被官方推托了事;劳工局就是有意进行调查,也未必能掌握资方违法事实。但假如劳工自身有着充足的力量,自身就拥有着“工会”组织和雇主谈判、谈判不成以罢工抗衡的实力时,根本不须政府介入、也不需要法律保障任何权利,就能够争得应有的权益。
再举一例,当人民的言论自由此一人权遭到政府箝制时,依照目前的法律体系,依然必须要寻求政府,透过提起诉愿、行政诉讼等才可救济,在“官官相护”的保守逻辑下,当然是缘木求鱼。还不如组织人权倡议团体,厚植人民力量,向官方请愿或抗议,要求开放言论空间,才有一丝改革的可能。但这样不求政府的“人民权力”、“工人权力”,是以权利概念进行的改革时常忽略的根本关键所在。
更抽象来说,在讨论权利定义时,我指出:政府立法保障特定权利,是要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规范出特定的社会秩序。用抽象的概念来说,就是要以“应然的律法”,来规范“实然的现实”。
但我们必须承认,“应然的律法”和“实然的现实”,总是存有着落差。虽然以权利语言写成的“应然的律法”,有一定可能地介入“实然的现实”,但也高度可能在各种社会条件下,所能介入的程度有着巨大局限。这两者间的落差并不会理所当然地消逝,甚至我们可说,总有着一种“永远无法弥补的落差”——法律或权利的改革,永远无法完整救济层出不穷的侵害。
釜底抽薪之道,是受压迫的人们真正握有了“权力”,改变了社会的现实状况——弱势者不再弱势,劳工不再受资方予取予求,人民不再受政府单方宰割。而不只是让受压迫者有法律上的“权利”,只能改变“应然的律法”,但未必及于“实然的现实”。
(待续)
本文作者为英国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社会学博士生
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198
关于我们
本刊将秉持理性、平实的方针,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民众的维权活动,对社会焦点问题进行分析评论;同时普及宣扬人权理念,系统介绍国际人权法律知识和维权案例,推动法制建设,扩大公民社会的空间,为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服务。
过往各期
六四专题
搜索
热门转载

-
时事大家谈:赞“一士之谔”,中纪委反击中宣部?
-
小品:讨伐任大炮
-
魏京生: 任志強很勇 如同自己當年
-
任志强: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式分析
-
微自由: 任志强微博被封
-
《大炮有约》01 尼玛开撸,戴上头套谁敢惹咱俩
-
《大炮有约》任志强:不怕向任何人开炮
-
【中国情报】肃清微博大V | 中国走向法西斯二次文革? 20160301
-
批习「媒体姓党」遭清算 任志强微博被封 学者:已到二次文革边缘
-
党媒批任志强暴露党群对立

-
国土国家在茅于轼手里吗?
-
12国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
-
12国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
-
12国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