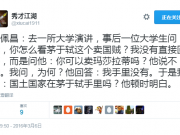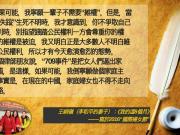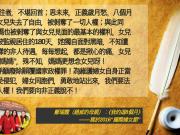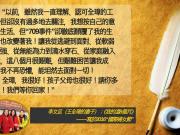敬告读者
为更有效地使用资源,《中国人权双周刊》从第181期起并入中国人权主网页。网址是:http://www.hrichina.org/chs。我们将继续遵照本刊宗旨和编辑方针,一如既往地为读者服务。
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泣血的“草根声音”(三十三)
——北大荒垦区上访问题调查
(接第143期)
第十四章 历史在倾听和等待
——黑龙江省调查组听证会实录
2010年12月下旬,根据黑龙江省委领导批示精神,省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奔赴北大荒垦区,就我所写《疼痛的黑土地》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听取意见。事情进行到这种程度,我自然成了“信息中心”,接受调查核实的农工不断把各种动态和信息反馈到我这里。自《疼痛的黑土地》风声传到北大荒以后,每天我的手机响个不停,有我访谈过的,有我没见过面的……
黑龙江省调查组下去以后,农工们十分感动,觉得终于有人管他们的事了。他们说,调查组的工作作风是深入的,态度是认真的,工作方式是公开、透明、坦诚的,调查对象都是《疼痛的黑土地》中的讲述者——我访谈过的农工。
农工们的心情非常高兴和舒畅,尽管2010年的冬天如此寒冷,北大荒雪深盈尺,他们依然像盼来久违的艳阳天一样。龙镇农场于德清、红色边疆农场吴延敏、引龙河农场唐维君等人说,这些年“告天天不应,告地地不灵”,奔波劳苦,伤心落泪,拘留劳教,挨整挨骂,“真是郁闷死了”。看着电视上国家到处一片繁荣景象,而我们年年月月一家人“从来没舒心过,这回上边来领导了”,终于有人以郑重、平和、耐心、公正、亲切的态度,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让他们畅所欲言,“吐吐心中的苦水,看来有希望、有盼头了!”
建三江分局所属的大兴农场、洪河农场、红星农场也有农工来电话问:“能不能让调查组也到我们这儿听听意见啊?”(2010年12月下旬,我去哈尔滨完成一项写作任务,期间大兴农场、洪河农场、前哨农场、前进农场、胜利农场有50多位农工到哈尔滨找我反映情况,还有很多要来的人,但多数被我的助手好言劝阻住了。)
省调查组首先到达北安分局。
其工作方式类似“听证会”。黑龙江农垦总局信访办主任任少军等人一路陪同,所到之处,分局领导、农场领导、相关业务部门专业人士,以及我访谈过的农工共同参加调查会。农工们谈意见和诉求,农垦官员做解释、讲理由和根据,双方时有交锋。这样做是正确和便捷的——便于调查组充分了解官、民双方各自的观点,核对事发经过,听取有关证据、依据。
与会农工那种渴望、振奋、重视、战战兢兢的心情可想而知。因此有人录了音,有人做了记录,连调查组到农场调查时,来了几辆车和车牌号都记下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调查组决定着他们的命运与未来!
过后,与会农工们把记录材料发到我的电子邮箱。
读罢这些详实、真切的现场记录,我感慨万端:
其一,这样的听证会,垦区系统大小官员加起来常常是二三十人,而到场农工只有三五人,闻讯而去要进会场向调查组反映情况的其它农工都被垦区公安人员拦在门外,理由是“调查组见谁,都是点了名的”。可以想见,听证会现场,从人数、官职到场面、气派,那种不对称的无形的威慑力,肯定会给农工心理带来种种影响。但是,我不能不向这些农工表达我深深的敬意。会上,他们表现出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十分镇静、理性的态度。而且经过多年上访,他们已然成了“法律专家”,引经据典,条条是道——这样的老百姓越多,中国的事业和前途就越有希望!
事实是对质出来的,真理是比较出来的。为便于读者考察了解我的调查报告是否属实,并客观了解垦区官员和农工各自的意见与观点,从而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断,现将与会农工提供给我的录音或会议记实,摘要录之如下。
1、黑龙江省委调查组赴北安分局所属龙镇农场调查会纪实
(事见本文第四节)
时间:2010年12月28日下午2点50分。
地点:龙镇农场会议室。
参加人员:黑龙江省调查组宋组长等3人;农垦总局信访办主任任少军、林业局满副局长等多人;北安分局王副局长、徐副书记、林业处孙艳波处长等多人;龙镇农场王立军场长、石书记、韩副场长、政研、林业部门等十多人。
退耕还林农户:于德清、刘玉云、刘兴华、王义锋、傅继生、王红彦6人。
下午4时,6家退耕还林户被韩副场长引入会议室,韩事先告诫6户农工:“反映问题要简单,不要乱说。”
调查组宋组长:“你们反映什么事,有什么要求?”
于德清:“1、我们要求龙镇农场给我们落实退耕还林政策,全部给付各项退耕还林补助;2、要求龙镇农场把《造林合同书》中有关农场与我们‘三七分成’的条款取消;3、要求农场赔偿因该场违约给我们6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30多万元;4、要求享受国家给予的林业燃油、护林防火及各项林业惠民补贴。”
宋组长:“你们是要退耕还林补助吗?”
于德清:“对,我们要每亩50元苗木费、200斤补助粮、20元生活补助费。”
宋组长:“这个问题谁来解答?”
分局林业处孙艳波:“这个问题我说过多次了,我还说说吗?”
宋组长:“说说吧, 当着大伙的面说说。”
孙艳波:“这个问题我和他们说过不止一次。”
宋组长说:“是多次吗?”
孙艳波说:“对,是多次。农场是国有农场,是全民所有制,包括承包种地的,人人都有受益权,农场代表国家行使土地管理权,是土地经营权人。根据《国有农场条例》第3条、第10条和《退耕还林条例 》第35条:‘国家按照规定的退耕还林面积,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提供粮食补助、种苗造林补助和生活补助。’所以农场应享受退耕还林政策。”
于德清:“刚才孙局(处)的说法不够准确,多年来他只接待我们一次,而不是多次。农场是全民所有制,但并不是说你是全民所有制,就可以侵权。农场代表国家行使土地管理权,对外发包土地,人人都可以承包经营。再说,土地经营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退耕还林条例》第35条规定是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提供补助粮食、种苗造林补助和生活补助’,而不是向土地经营权人提供。因此孙处长的说法是偷换概念的说法,因此说由农场享受退耕还林政策的理由不能成立,于法无据。这片退耕还林的土地是我们95年开始投巨资承包、开垦、改造和熟化的,也是经发包方龙镇农场再三动员而实施的。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是我们违约而是龙镇农场多次出尔反尔,违背合同约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我们刚开垦还没熟化,农场就让我们栽树,以防被林场收回。为了平息地方矛盾,农场于我们的切身利益而不顾,今天让我们栽树,不栽树就收回开荒地。明天告诉我们不准栽树,谁栽树就收回谁的开荒地。换一茬领导,下几茬命令,朝令夕改,使开荒户苦不堪言。再加上天灾,使我们生活举步维艰,取借无门。有人为躲债远走他乡,有人丧命于开荒之中。我为开荒曾几天吃不上一顿饭,为解饿,我到别人瓜地想赊点瓜吃,因为没钱,让人指桑骂槐没赊给,我只好忍饿含泪离去,我穷得冰天雪地只好穿单鞋过冬。大多数开荒户由小康家庭变成了穷光蛋。各位领导,我们为了响应国家五荒开发,不但投入了多年积累了几十万元的积蓄,每户还背负了几十万元的债务。我们每户为此都投入了上百万元的资金,难道说农场让我们投入的资金还能用笤帚划拉回来吗?1995年,场长在开荒开始时对我们说:‘将来开荒地归你们长期使用’。因为当时的开荒政策是谁开荒谁拥有。开荒地刚熟化过来,正逢国家退耕还林,根据新出台的林业政策,龙镇农场强迫我们退耕还林。2002年9月12日,农场召开退耕还林动员会,主管场长说:‘谁不退耕,就收回谁的承包地!国家可能有退耕还林待遇给你们,以便缓解你们的实际困难。’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和龙镇农场签订了30年的退耕还林合同。合同签订后,农场没当场发给我们,说盖完章后再发给我们。就此我们多方筹借资金,到处购买树苗,几乎走遍半个黑龙江省。2003年4月25日,我们全面完成了植树造林。可农场就是不发给我们合同。几经多次催要,农场在5月25日才将背后偷改‘掉包’的合同发给我们,结果‘退耕还林合同’变成了‘荒山荒地造林合同’。04年2月,我们多次找农场理论,对农场上述欺诈行为非常气愤。当时农场找来农垦北安分局林业处何工,否认我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身份。由于当时我们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概念不清,我们问何工我们是什么?何工说我们是‘退耕还林者’。现在用他们的说法,我们连‘退耕还林者’都不是了。为去除显失公平的合同条款,我们双方对合同进行了4项修改。可是龙镇农场再次乘合同盖章之机‘掉包’合同。我们发现后非常愤恨,就此上访,多次找北安局,林业处何工一语道破天机说,我们不加上‘合作造林’,用什么理由来享受退耕还林政策?难道说他们单方塞加‘合作造林’,就成为享受退耕还林政策的理由吗?龙镇农场利用职权弄虚作假,实施合同欺诈的违法行为,直接损害退耕户的合法权益。在座的领导,请看‘退耕还林工程’标牌:承包人是我,这个标牌不是我于德清造的,是龙镇农场竖的。从承包人变成了合作造林,这到底是为什么?让龙镇农场及垦区相关领导为此上下串通,颠倒黑白,捏造事实,制造谎言,甚至疯狂。我们认为,是为的这十几亿的退耕还林资金!”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4期 2014年11月14日—11月27日)
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22957
关于我们
本刊将秉持理性、平实的方针,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民众的维权活动,对社会焦点问题进行分析评论;同时普及宣扬人权理念,系统介绍国际人权法律知识和维权案例,推动法制建设,扩大公民社会的空间,为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服务。
过往各期
六四专题
搜索
热门转载

-
时事大家谈:赞“一士之谔”,中纪委反击中宣部?
-
小品:讨伐任大炮
-
魏京生: 任志強很勇 如同自己當年
-
任志强: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式分析
-
微自由: 任志强微博被封
-
《大炮有约》01 尼玛开撸,戴上头套谁敢惹咱俩
-
《大炮有约》任志强:不怕向任何人开炮
-
【中国情报】肃清微博大V | 中国走向法西斯二次文革? 20160301
-
批习「媒体姓党」遭清算 任志强微博被封 学者:已到二次文革边缘
-
党媒批任志强暴露党群对立

-
国土国家在茅于轼手里吗?
-
12国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
-
12国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
-
12国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