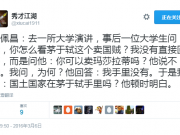敬告读者
为更有效地使用资源,《中国人权双周刊》从第181期起并入中国人权主网页。网址是:http://www.hrichina.org/chs。我们将继续遵照本刊宗旨和编辑方针,一如既往地为读者服务。
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不虚此行
——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二)
(接第87期)
第一章 收 容
2007年4月24日早晨,一辆警车载着我们11个人从海淀区拘留所出发,一路上拉响警笛、闪着警灯疾速向南行驶。
我闭着眼,趴在堆放在过道上的行李上,听着别人聊天。李亚斌已经是第三次被劳教了,她和一个第五次被劳教的男犯人很熟悉,他们说着说着突然话题转到我了,那个男犯人说:
“老太太,你进去以后可得乖乖地听警察的话,人家让你写什么就写什么,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李亚斌打断了他的话:“她不是法轮功,是那拨上访的。”
“啊,是‘新国大’的呀!大姐。”刚才还管我叫老太太呢,马上又叫大姐了。
他又说:“你要是法轮功可就受罪了,如果不写‘三书’(我后来才知道‘三书’是悔过书、决裂书、保证书),你就被包夹,那就惨了。”
“什么叫包夹呀?”我奇怪地问。
他说:“就是4个人围着你坐着,你站在中间,一点儿也不许动。就让吃四分之一的馒头,只给喝一点儿菜汤。你站不住也得站,往哪边倒都有人揪着衣服。”
“真的吗?警察还干这个?”我有点儿不相信。
李亚斌说:“警察才不干呢,劳教最可怕的就是群众斗群众。只要队长一句话,整人的花样多了。”
在拘留所的监室里就听那些二进、三进的人讲了很多调遣处怎么折磨人的事,都说在调遣处3个月就得脱一层皮。听着那些恐怖的故事,吓得我心脏砰砰乱跳。
当我亲自体验劳教生活之后,才知道准确的表达应该是:不是脱一层皮,是只剩一层皮!
我的体重从55公斤变成了40公斤;我的腰围从77公分(2尺3寸)变成了57公分(1尺7寸);手像鸡爪子、肋条骨像搓衣板、脸上的皱纹像一条条刻痕。腹部松弛的皮可以卷起来,晚上仰卧在床上,凹陷的肚子可以倒入一碗水。我摸着蠕动的肠子,它一会儿硬、一会儿软,很奇妙。
李亚斌指着调遣处的大门说:“到了,这叫凯旋门。”
警车开进了院子,停在了西面的一座房子前面。我们的手铐被打开了,男女劳教人员立即被分开排队。大家把自己的行李放在脚前面的地下,就被带进房子检查身体,原来这是一个医院。
检查完身体,刚走出医院的门,就看见院子里几十个男的齐刷刷地蹲在地下,两手在后脑勺交叉抱着头,把脸贴到膝盖上。两个警察手持电警棍来回走着,不停地吆喝着“老实点!”、“低头!” 一个警察喊话了:“把证件、钱包、钥匙、手机,值钱的东西拿出来,举起来。”那些男的迅速地翻着自己的行李,有的找出来了,立即伸长了胳膊举起来;有的把那些东西攥在手上,继续抱着头,拿着东西的手从脖子后面向上举着。伸长了胳膊的显然是第一次被劳教的,马上就被握着电警棍的警察训斥:“看看人家是怎么拿的?”顿时,一片人头的后脑勺顶上长出了各种各样的钱包、手机、钥匙……
我们6个女的被带到自己的行李前,“蹲下!”还好,没让我们抱着头。
我的膝关节已经退行性病变了,只能半蹲着。刚蹲了几分钟,腿就没有知觉了。
海淀拘留所的警察办完了交接手续要走了,一个警察走过我身边说:“这里可厉害,你可要小心!”我茫然地说了一声“谢谢”,霎那间出现了一个幻觉,好像他是来接我回去的。
一个戴着隔离帽、穿着长长的隔离服、戴着隔离手套的女警察拿着一张纸,叫了三个名字,有我。让我们把自己的东西都带好,三个人大包小包的背着扛着跟着她往D楼走去。
关键词:自愿抛弃
九大队在D楼的一层,上4层台阶就可以进入大门。大门是铁制的,上部是玻璃,玻璃上写着“收容人员专用通道”。
一进门就是一个长约13米、宽约9米的大厅。大厅的西面是筒道,我们被直接带进筒道北面的第一间屋子,叫北一。
一进屋,一个劳教人员就让我们把被褥铺在地上,把其它物品放在被褥上。我看见她胸前戴的牌子上写着“代元元、吸毒、36岁”。
警察命令我们脱光衣服,祼体站着,按照她的命令转动身体,警察和代元元仔细地查看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李亚斌的臀部有一个伤疤,被她们记录在一张纸上。秦永红的后背有一块胎记,也被记录。问我身上有伤疤没有,我说没有。我又想起来颈部做过甲状腺线切除的手术,就说了。马上被训斥:“刚才问你你说没有,这会儿又说有,以后想好了再说。”她们仔细看着我的脖子,却看不出手术后的痕迹,商量着记不记,最后还是做了一个记录(后来我瘦了,脖子上的每一根筋都暴露出来,这个手术痕迹就清晰地显现)。
四月的天气还很凉,这间屋子又是北面,一丝不挂地站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开始发抖了。幸亏检查完了,我赶紧拿起背心要穿,但被警察制止了。她说这件背心的图案太花了,不让穿。我说这只是印有奥运五环图案的白背心,她说颜色鲜艳、不行。我只好又拿起一件白色的背心穿上。穿完了秋衣秋裤,我又拿起毛裤要穿,又被她们阻止了。代元元给每人发了一身灰蓝色的涤纶队服和一双松紧口的黑布鞋,就让穿这些。我一直穿着毛衣毛裤,现在只让穿单衣,感觉很冷,就说因为冷,想多穿点衣服。可是警察说:这里不让穿毛裤,你的毛衣是系扣子的也不让穿。我的行李中还有一身紫红色的班尼路的绒衣绒裤,就拿起来,可是警察又说:这里不让穿颜色鲜艳的。我只好要求再穿上一件秋衣和一条秋裤,警察说:“你怎么这么多毛病啊,你看见谁穿两条秋裤?”
接着,有两个劳教人员开始清理我们的物品。从拘留所带来的东西几乎都不让留下,只给我留下了卫生纸和一条裤衩、一身秋衣。本来是成卷的卫生纸被抖开,像一堆烂布条。
我的防雨风衣、羽绒坎肩、毛衣毛裤、绒衣绒裤、毛巾、牙膏、水杯、肥皂及肥皂盒、软底皮鞋、袜子还有那件奥运五环的大背心等穿的用的,还有从拘留所带来的两袋牛奶、一包花生米、一袋维维豆奶等都让我“自愿抛弃”,说这里发生活用品,新来的劳教人员没有资格吃其它食物。我舍不得扔掉那些衣服,就问:“能不能等家里来人见面的时候带回家?”警察不高兴地说:“半个月以后才让接见呢,这么多东西没地方给你存放!”我想用我装行李的大布袋装这些东西,也不让,说只能用这里的塑料袋装,一个人就给一个塑料袋。
我看见和我一起来的李亚斌的4、5瓶洗涤灵、十几块香皂和肥皂,还有40袋洗发液也被“自愿抛弃”了,秦永红的许多物品也都自愿抛弃了,于是,我赶紧把儿子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的羽绒坎肩和其它几件我实在舍不得扔掉的衣服往塑料袋里装。这几件衣服就塞满了塑料袋,其它的东西只好不要了。每个人都必须在一张纸上写“以上物品是我自愿抛弃”并签名按手印。这个过程叫“清身”。
这一天一共进来了7个新生,清身之后都坐在大厅西侧的两排小椅子上,面朝西墙。我们被要求按“规范坐姿”坐好,坐姿是挺直腰板、两腿并拢、脚跟靠齐,双手平放在大腿上。我大约只过了十几分钟就觉得腰酸腿软屁股疼,从肩膀一直到胳膊都麻木了,两只手胀得难受。我很想活动一下,又不敢,因为刚才有几个人已经被训斥了。我们被规定不许东张西望,不管旁边出了什么事都不许看。
但是我还是悄悄地观察着这个大厅。我面对着的是西墙,雪白的墙面一尘不染;脚下是以绿色为主色的、由黑白黄绿的小碎石组成的水磨石地面,亮得能照出人的影子。水磨石被玻璃条隔成一大块一大块的,每块的边长大约有80公分。
我们被告知:等一会儿队长要找你们谈话;对本队的警察要叫“队长”、本队之外的警察要叫“领导”;进门之前要站在门外大声喊“队长好,报告队长我能进吗?”听见队长说“进”之后,要说“是,谢队长。”特别强调,要说“谢队长”,不许说“谢谢队长”。值班员带着大家练了几遍,我很不习惯说“谢队长”,总是说“谢谢队长”,当然少不了被人嚷嚷几句才学会说了。
四个小哨和三个委员(警察用来管理其他劳教人员的劳教人员)轮流问我们同样的问题——“姓什么叫什么,什么罪错……;住址、电话……”等等个人的基本情况。我很奇怪,也一阵阵心烦,怎么这么多人重复地不停地问同样一个问题呢?我想:你们也是劳教人员,这些内容该你们问吗?你们和我一样被劳教,我凭什么告诉你们哪!后来才知道,她们每个人都把这些情况记录在自己的本子上,要迅速地记住每一个新生的情况。当队长想了解什么人的情况时,她们会马上告诉队长这个人的基本情况。因为如果她们说不清楚别人的情况,她们也要被队长训斥。
我被问到第四遍时,心里已经很烦了,可是还得强耐着性子回答她们的问话。
大家陆续地被带到筒道里的其它房间谈话。我被一位李队长带到北四去谈话。北四是一间库房,里面排列着很多长方形的小柜子,是给劳教人员放东西的。我站在两排柜子中间,李队长坐在一个小椅子上,边问话边记录着。她让我说说犯罪过程,我就说3月4日在全国人大开会的前一天去了中央电视台就被抓了。
她说:“我问你话,你要如实报告,不许弄虚作假、欺骗干部。”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小心翼翼地问:“李队长,您觉得我哪句话不真实?”
她说我被抓的内容不真实。我说保证是实话,如果以后查出我说假话,我愿意承担责任。
问话进行了很长时间,我的腿有点儿站不住了,就在原地活动了几下。
李队长批评说:“我跟你谈话呢,不能乱动,你要动先喊报告。我允许了才能动。”
这时候,李队长看见我的齐腰长发就说:“你的头发要剪掉。”
“可以不剪头发吗?”
“不行,到这儿必须剪头发。”
“为什么要剪头发呢?”
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露出了一圈白眼球,从眼镜片的上面看着我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奇怪,从来没有人问过为什么剪头发。所有的人都剪,就是必须剪!从卫生的角度上讲也得剪头发呀。”
我说:“我能保持卫生,可以不剪吗?”
“不行,必须剪!”她语气坚定、目光严厉地说。
我的心头一阵冰凉。
自从2003年10月22日我因为到中南海西门给胡锦涛送信被逮捕,关押在西城区看守所时就开始留长发了。我非常喜欢我的头发,我的长头发像瀑布一样飘逸在腰间。
在到调遣处之前,李亚斌她们就已经把头发剪成了男式短发,可是我不相信现在还必须剪头发,因为在2004年就有明文规定,被判三年以内刑期的罪犯可以不剪头发。那么被劳教的期限最长才三年,又不是罪犯,就更不应该剪头发了。我就请海淀拘留所的杨所长帮我问问调遣处:现在还剪头发吗?杨所长当时就说:不用剪头发,哪能这么没有人性啊? 我就相信了他的话。可是没有想到,到这儿来还是要剪头发。
在墙角还有两个人。我的头虽然不敢转动,但是我的眼珠向右面一转就可以看见她们。
一个人面朝墙笔杆溜直地低头站着,可是她的鞋跟却没有提上,而是被脚后跟踩着。雪白的袜子踩着黑布鞋,特别显眼。后来才知道,她叫张小敏,因为晚上洗漱完了回班后穿着布鞋、踩着鞋后跟在班里走动时被队长发现被罚。
另一个人面朝墙坐在一个没有靠背的蓝色塑料方凳子上(后来知道这种凳子叫“高板儿”),她左脚的脚尖着地,右腿搭在左腿上,就像常说的翘着二郎腿。她俩像雕塑一样,保持着这样的姿势一动不动。
也不知道是几点了,我在进出大厅和筒道时,悄悄地抬眼看四面,没有找到钟表。从太阳光射进窗户的位置看,大约是11点左右。
“大厅的放茅!”筒道里传来了一声命令。
“是——”,那两个人大声地拖着长音回答。随着回答声,两座雕像活了起来。站着的慢慢地弯腰提起鞋后跟,又慢慢地直起腰,两条腿活动了几下;坐着的用两只手抱着架在上面的腿,轻轻地把它挪下来,然后转身用手撑着高板儿,两只脚不离开地面交替抬起放下,好像很费劲地站起来。
我正看着她俩,又听见喊:“你们都哑巴啦,没听见‘大厅的放茅’?不放就算了,等着下午一块儿放吧!”我这才反应过来,“放茅”就是上厕所;“大厅的”就是我们。我早上一进来九大队就问过厕所在哪儿,可是听到的是“等着,统一去。”好不容易等到让上厕所了,又因为没有回答“是”就不让上了。我赶紧说:“报告班长,我憋不住了——”,几乎是同时,王晓丽和其他几个人也说出了同样的话。我们又被教训了几句,又喊了几遍“是”,才让站起来排队放茅。
我们都扭动着身子走路,大家的腿好像都麻木了。我们的手被要求按“规范”紧紧地贴在大腿的两侧,不许摆动。大家低着头排队在筒道里走着。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走路姿势,说不出来像是一帮什么人。有人可能是朝筒道两侧的屋子里看了,“低头,不许看!”的喊声又传来了。
厕所在筒道的北面,有23个蹲便池,南北两排,但是只让用北面的一排。我们被告知“现在和下午2点放茅的时间可以放大茅,其它放茅时间只能放小茅,不是放茅的时间不许放茅。”
我小便完了,站起来。有几个人已经上完了,在过道上排队等着。王晓丽和那个胖老太太还没完,小哨又喊起来:“快点儿,就等你们了。”
王晓丽带着哭腔说:“我憋的时间太长了,尿不出来。”
“尿不出来就别尿,到点了,队长该来锁门了,就因为你们耽误大家呀?”
胖老太太也完了,王晓丽还没站起来,小哨站到她的面前不停地催她。
王晓丽哭起来:“你越催我我越尿不出来,你站在这儿看着我,我更尿不出来了。”
上完厕所,我们被带到隔壁的水房洗手,这是午饭前统一洗手。
这使我意识到,今后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大便问题,因为我患有小肠综合症:当我感觉到要大便的时候,连几分钟都等不及,大便都是不成形的稀便,有的时候肚子还剧烈地疼痛,可是便出来之后就不疼了。为了治疗这个毛病,看了许多医生,吃过许多中药、西药也没有效果。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大便,甚至在吃饭时肚子就疼痛起来,必须放下饭碗去大便。如果要有室外的活动或乘坐公共汽车,我都不吃饭。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后来这竟然成了警察虐待我的手段,让我承受了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和身体的巨大的痛苦。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8期 2012年9月21日—10月4日)
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2493
关于我们
本刊将秉持理性、平实的方针,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民众的维权活动,对社会焦点问题进行分析评论;同时普及宣扬人权理念,系统介绍国际人权法律知识和维权案例,推动法制建设,扩大公民社会的空间,为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服务。
过往各期
六四专题
搜索
热门转载

-
时事大家谈:赞“一士之谔”,中纪委反击中宣部?
-
小品:讨伐任大炮
-
魏京生: 任志強很勇 如同自己當年
-
任志强: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式分析
-
微自由: 任志强微博被封
-
《大炮有约》01 尼玛开撸,戴上头套谁敢惹咱俩
-
《大炮有约》任志强:不怕向任何人开炮
-
【中国情报】肃清微博大V | 中国走向法西斯二次文革? 20160301
-
批习「媒体姓党」遭清算 任志强微博被封 学者:已到二次文革边缘
-
党媒批任志强暴露党群对立

-
国土国家在茅于轼手里吗?
-
12国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
-
12国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
-
12国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