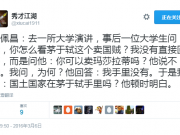敬告读者
为更有效地使用资源,《中国人权双周刊》从第181期起并入中国人权主网页。网址是:http://www.hrichina.org/chs。我们将继续遵照本刊宗旨和编辑方针,一如既往地为读者服务。
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朝鲜难民宋利辉
2009年10月,我因经济窘迫不得不迁居农塔布里,那是西北方向紧邻曼谷的一个镇,同类房租比曼谷市区便宜一半以上。我的新居所在联合国难民救济机构推荐的一所公寓楼里:它是一幢四层旧楼,阴暗恶臭,楼下垃圾成堆,镶嵌于外墙上的旋转式铁楼梯锈迹斑斑、摇摇晃晃,楼内走道拐弯处墙上的一组组气孔被奇怪地以水晶塑料堵死;整幢楼住的多数是贫困的难民和难民申请者,有黑人、越南人、柬埔寨人……还有逃避计划生育迫害的中国农民,他们基本上没有讲究卫生的条件;剩下的就是泰国的穷人和不务正业者,其中有混混、酒鬼、吸毒者,还有疯子。因此,这幢楼与其说是公寓楼,不如称作难民营或贫民窟更贴切些。我在中国住惯了居民小区公寓楼,突然住进这种地方,深有沦落的感觉。
有一天下午,外出办完事后,我沉闷地回到这幢阴暗的楼内。身后突然有个男人的声音在走道内向我热情地打招呼,是怪腔怪调的普通话。那腔调既像河南腔、又像山东腔、也有点像辽宁腔……总之是啥都像,也可以说是“四不像”。我闻声不由得浑身一紧,放射出受骚扰惊吓者的本能反应,猛回头,只见身后上来一个身着短裤背心的矮壮汉,那红背心像中国70年代的那种老土式样,他样子50岁左右,长脑袋很大、前额微凸、尖下巴、蒜头鼻,在楼内昏暗的光线中,一双如玻璃跳棋般的溜圆小眼睛闪现出昏浊的光。他的身材和容貌像中国南方人,但白里透红的皮肤却是北方人的特征。
“请问你是哪位?”话虽然礼貌,我的生理已经处于备战状态。
“我是新来的,是你的邻居,昨天搬来。BRC(曼谷联合国难民救助机构)的人带我来住,我也是难民……”他说的普通话有些怪异的生分感。
“你怎么知道我是中国人?”我更加怀疑了。
“BRC有个练法轮功的翻译说,有个中国广西来的记者,头发很少的,也住在这里。我猜就是你,哈哈……昨天晚上我听见你打电话,你说广西话呀……”
“你是中国哪里来的?”我问。
“不是,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朝鲜人,我父亲是中国人……”
一听是朝鲜人,我绷得紧邦邦的阶级斗争弦一下松弛下来,自忖道:中共再胡来,现在还不至于用朝鲜人对付我等书呆子吧?对这个陌生的朝鲜人,我这个前记者来了兴趣,就像闻到桂林马肉米粉的香味一样。我在老家——国际旅游城市混到30多岁,欧美各国人等都有接触,就是没接触过朝鲜人;我在曼谷做难民一年多,见惯了索马利亚、斯里兰卡、伊朗、柬埔寨、越南等各色难民,就是从没碰到朝鲜难民——我心里早有一个疑问:难民大国朝鲜的难民,都藏哪里去了?
于是握手言欢、开门延客、请坐上果,一连几天畅谈尽兴。一时间,我们两个中朝难民,就好像毛泽东和金日成那样“亲密无间”。这个朝鲜人对中国人有些好感,因此采访颇为顺利,但他又有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性格,因此也存在风险,幸而,我抢在他的“同志加兄弟”好感变为恶感之前,好歹绘成了一幅素描像。
此兄2009年7月份得的难民资格,刚由联合国从移民局监狱保出来,身无分文、没有活路,就往难民署门前一躺,吓得联合国官员赶紧给他“特事特办”,发给他每月2500株的难民费,让工作人员带他到此“BRC推荐处”入住。
此兄自称宋利辉,1952年生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母亲是朝鲜国民。1973年的一个寒夜,宋利辉跨图们江逃亡朝鲜,从此成了朝鲜国民。
宋:我妈是朝鲜人。我出生之前,大概是1951年,我妈带着一个4岁的孩子——就是我的同母异父的哥哥,跑到延吉——因为朝鲜打仗(指朝鲜战争)呀,很可怕。在延吉,她嫁给一个汉族人,叫宋国龙,祖籍是山东的,他就是我父亲。我快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搬到图们去,我父亲在铁路工作。
1955年,中国政府要延吉的居民定国籍,让我们自己选,我们要了中国籍,我母亲选了朝鲜籍,她每三年回一次朝鲜。就因为朝鲜国籍,文革中我妈被打成“朝修特务”,他们都被批斗,挂着牌子游街,被拳打脚踢……延边地区整人很厉害,我记得自治州州长宋德海,还是中共中央委员,文革中都被整死了。
因为我妈是朝鲜人,很多亲戚在朝鲜,我们就受到歧视——不准入团、不准入党、也上不了大学。我读书只读到初二就不读了。1968年,我下放到吉林珲春农村,那地方离朝鲜只有60里地,一面是高山、一面靠河,那条河叫红旗河……
(宋利辉操着他那“四不像”口音的汉语,吱吱呀呀地述说着陈年往事。他的声调如他的下颌一样尖而突出,时时奇怪地上扬,那种倔强执着、刻板持久,有点朝鲜泡菜的味道。宋利辉说,他的这口汉语在延边学成,那时延边学校里用汉语教学。尽管学会了汉语,他却在中国呆不下去。)
我1971年回城,安排去当建筑工人——吉林那边的建筑工地不用竹竿,只用松树杆。我工作很卖力,工资上调到39块钱每个月,吃45斤的定量粮,这在当时很不错了呀!
曾:那你怎么还要走?
宋:没有政治前途呀!那时候,没有政治前途,什么前途都没有,干得再好也没用!我出身有问题,怎么也不会提拔的。
曾:你什么时候去的朝鲜?
宋:1973年。图们市去朝鲜容易,就隔着一条图们江,最窄的地方10多米;图们江朝鲜人也叫“逃亡的江”,往北流。现在许多朝鲜人跨过图们江跑来中国,那个时候是中国人跨过图们江往朝鲜跑,“3年自然灾害”(指毛共“大跃进”导致的1959-1961年大饥荒)时期,一百多万中国人逃到朝鲜,一百多万呀!你不要以为你们中国怎么样,一直到80年代初,朝鲜还比中国好,还有中国人逃来朝鲜……
曾:你那时候游过图们江?
宋:没有。图们江每到冬天就全部结冰,很厚的冰,一直到3月份,冰还有10厘米厚,我就在晚上溜冰过去,上岸就是朝鲜咸镜北道……
曾:你就这么丢下父母走了?
宋(那张尖下颌的丰润脸庞扭曲了):嗨呀!没办法呀!我跑了以后,我父母罪加一等,1973年元旦夜里两个人喝农药自杀了。我很久才知道父母死了,1986年,我带着8岁的儿子回延边探亲,家乡人告诉我父母早死了。我在中国没有亲戚了……哎呀,你问这个干什么呀!?哪有像你这样问的?联合国都没这样问呀……(老宋突然脾气来了)
(我知道我的草率触痛了老宋内心深处的创伤,抱歉之下,急忙转问他在朝鲜的新鲜事,希望借此调节气氛,另外,我也急于想了解普通朝鲜人的生活究竟怎样。)
宋:过到朝鲜后,我就去珲宁投奔亲戚,图们江到珲宁两百公里——从珲宁往南,就必须办护照了。我有很多亲戚在咸镜道,我就在这家住两年,那家住两年。那时逃到朝鲜的中国人,3个月之内必须去警察那里登记,申请身份,朝鲜的公安局叫保卫部,派出所叫安全部。我在朝鲜一样当建筑工人,很积极,公司就送我去读大学,我在大学学的是朝鲜语……
曾:不错呀,过得比在中国好。
宋:好什么呀!?朝鲜一样没有政治权利。朝鲜没有改革,很多做法比你们中国还恶劣。我认得一个朝鲜难民,在加拿大发了财,寄50万美元给家里,结果这笔钱全部被保卫部没收,家里人还受到警告。
我们中国来的人受歧视,不准入团、不准入党、不能提干,他们不信任我们。我1979 年拿到了朝鲜身份证,到了1986年,他们还想要我走,保卫部的人通知我说:中国现在不会害你了,你最好回中国去。但是我不愿回去。因为朝鲜也有比中国好的地方:朝鲜读书不要钱,没有你们那样大的贫富差距;朝鲜没有计划生育,女人多生金正日还奖励;朝鲜没有很多污染,你们中国污染很重,污染得像什么呀!朝鲜人住房子很容易,只要结婚,就可以分到房子,不过现在也要钱了,很便宜,你们中国老百姓买不起房子……
曾(忍不住打断):饭都没有得吃,有房子有什么意思?
宋:没有饭吃是在1994年以后,以前我们过得比你们舒服。你们中国到处是下岗工人……以前朝鲜的产品有苏联买,苏联解体了,朝鲜失去了依靠,经济滑坡。1994年,金日成死了,很奇怪,金日成死了以后两年,朝鲜发大洪水,没有粮食,饿死几百万人呀!老百姓和军队都往中国跑,跑过去几十万人呀,后来中国赶紧调军队把边境封锁起来,不这样朝鲜劳动党就垮台了。
曾:你没受到影响吗?
宋:我在1993年就离开朝鲜了。我在朝鲜有钱,做生意;我1990年就办了护照,经常去中国、俄罗斯做生意,去海参崴、满洲里……1993年我去东南亚做生意,1997年从泰国南部跑到马来西亚,签证过期了,被警察查证件查出来,关进马来西亚移民局,后来转送到泰国和蔼移民局,在泰老边境。
有一天我出庭受审,我的包放在移民局监狱房间,回来以后包不见了,里面30万泰铢、朝鲜护照统统没有了,他妈了个X的!我的包一定是泰国警察偷的,在警察的眼皮下谁敢偷这样大的一包东西?和我一起被送来的缅甸人知道我的包有钱,一定是他们告诉警察我有钱!警察拿大头,分给他们一点儿。所以我对泰国印象很差,泰国警察真他妈的贪呐!我学马来语、缅甸语、柬埔寨语,决不学泰语!(老宋那两只昏浊的小玻璃球放射出灼人的光)
曾:(老宋所言应该不虚,因为有一天他给我看他的联合国难民证,页首印着“NON-NATIONALITY”字样。)没有护照,不能回家了?
宋:也不想回去了,干脆就申请难民。当时以朝鲜人申请,移民局监狱里有联合国官员办公,向他们递交申请。难民批下来以后,我想去加拿大,但是韩国不准,韩国大使馆一干涉,递进加拿大大使馆的档案又退回来……有的朝鲜难民自己去联系其他国家安置,韩国的使馆官员发现后就威胁:“你妈了个X再不停止,对你不客气了!”吓得不敢去联系了。韩国不准朝鲜难民去其他国家,在泰国的所有朝鲜难民都得送韩国,美国也让韩国这样做,因为他们是盟国呀。
所有的朝鲜难民都要经过韩国情报院的面试。韩国大使馆的官员收钱,有钱的先安排面谈,在韩国有亲戚的也优先。面谈的时候,有的人写错了父母的名字,就被怀疑是中国的朝鲜族人,韩国官员上来就打耳光、脚踢;在韩国大使馆,韩国人可以吸烟,朝鲜人就不行,谁吸烟谈话延期一个月;有的韩国女工作人员穿短裙,朝鲜人多看一眼,就要处罚,单独关一个房……
曾:啊!真的吗?韩国可是民主国家啊。
宋:(额下的小玻璃球再次燃烧起来)什么他妈的民主国家?比朝鲜还坏!世界杯韩国还弄了个第四名呢,结果怎么样?结果怎么样?连泰国队、越南队都输,1998年亚运会,我在曼谷看电视,亲眼看到韩国队输给泰国队……世界第四?好意思呀!
韩国大使馆打人,韩国人权委员会来调查,就我一个人敢说,其他朝鲜人都不敢,怕报复呀!韩国大使馆恨死我了。2001年,我获得韩国安置,在韩国只呆了3个月,就被他们送到中国……
曾节明:啊!?
宋:他们说,我父亲是中国人,韩国是单一民族国家,不接受中国人……这他妈什么道理呀!?住在韩国的中国人有10万人,还有在韩国申请难民的中国人,他们能住,我为什么不能住?
韩国人很可恶呀,你们中国人不知道,韩国是最排华的,朝鲜和日本都有唐人街,只有韩国不准有唐人街呀!……
曾:还有俄罗斯也不准搞唐人街……你在中国还好吧?
宋:我在中国呆了7个月。中国政府也不承认我,因为我加入了朝鲜国籍,但是中国政府也不赶我走。我在中国打工,湖南、广西——你老家,我都去过,柳州的鱼峰山我也去过……
(谈到柳州鱼峰公园,我不由备感亲切,我对柳州很亲——鱼峰山下,既有童年的回忆,又有大学时代于柳州获救助的经历,更有在柳州得人相助,逃脱因言罪厄运的运气……柳州简直成了我的福地。可对老宋来说,肯定是另一番感受了。陌生感不说,对他这样的人而言,中国再大也是囚笼,就是爬也要爬出去。)
我走路两个月,从中老边境走到泰国边境……(宋利辉伸出他那双满是硬皮疙瘩的赤脚,作为他低成本偷渡的证据;走路时,他脚上的鸡眼痛得他一瘸一拐。他正在申请BRC让他去曼谷医院做鸡眼切除手术。)
我被泰国警察抓住,查身份证呀,关进泰老边境的移民局,后来转送到曼谷移民局。我的朝鲜护照早就被偷走了,放在包里,在和蔼移民局被偷走的,连包一起呀!护照号记不住,泰国移民局联系朝鲜大使馆,朝鲜大使馆也不承认我,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就把我一直关……泰国移民局(指移民局监狱)比韩国大使馆好呀,每三天下去一次,可以买东西、踢球、打电话……
(老宋略微浮肿的老脸上绽现出笑容,我知道那是不一般的苦笑,那种奇特的苦,饱蘸于他的自鸣得意上:他开始吹嘘他在移民局监狱如何懂做生意——靠帮警察卖咖啡挣了“一大笔钱”、他如何痛打一个偷他钱的英国窃贼、他如何在狱中“掌握”几门外语,以至于参加联合国面试无须翻译——不过后来我亲眼所见,他讲的英语西方记者听不懂,他说的柬埔寨语,柬埔寨人也听不懂……慢慢地宋利辉吹得累了,高扬的尖腔普通话平缓了下来,他的痛苦流露也随之而常见化。)
宋:在移民局,你们中国人走得真快,特别是练法轮功的(宋利辉鼻翼的两道浅纹突然深深刻下,那种嫉妒,显然如海沟般的苦涩)。我1997年来泰国,中间在韩国呆了3个月、送回中国7个月,算起来,我在移民局总共关了11年,11年啊!……
(这是那次成功“会谈”的最后一句话。岂料,我们的这次谈话居然成了最后一次长谈。我还想了解的东西太多,宋利辉那口朝鲜普通话讲出的东西,显然不及冰山一角;但我当时一点儿不急,自以为可以在农塔布里住到上飞机那天,慢慢深挖宋利辉的材料。我很快就发觉:宋利辉很不愿谈他在朝鲜的生活,尤其是家庭。于是我另外找了一个时间敲开了他满是泡菜味的房间,在堆放着新华字典、韩语字典,和字如一堆堆钥匙串般的韩文书籍地板上寻空盘腿坐下,我试图详细了解朝鲜的生活,结果因为技巧的粗糙,把他大大地得罪了。)
宋:……通什么信?不能写信呀!朝鲜人不能收国外来信呀!……家?什么家呀!?家乡逃出来的人告诉我,我女儿死了,妻子儿子找不到了……别说了别说了,头痛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哪有你这么问的呀? ……算了吧,要写,我会自己写。
于是,那次不欢而散的谈话,成了我对他房间的最后一次光临。那是一个家徒四壁的房间,破旧的吊扇在轧轧地吵着,地上摆放着老宋写的美工字——他写的美工字像印刷出来的一样;当时他正在写信,寻求加拿大的安置,他已经手工制成了一个致加拿大大使馆的信封,比印刷厂的工做得还美。
事前,他曾邀请我春节去他房间包饺子,之后不了了之了。每当碰面,宋利辉依旧和我招呼、说话,但不再热情。他抱怨房东老板娘在水电费上宰人、更嫌时间难熬,说想搬到朝鲜人社区去住。
孰料,我倒因受不了新搬来的一户柬埔寨难民制造的噪音,先他离去;我搬走后不到一个月,从BRC官员口中得知:老宋不知搬到哪里去了。
“11年啊!”,这个声音至今仍然回响,好像宋利辉就在我耳边。它让我想起了童年电视剧《虾球传》中的一个镜头:虾球老父,于归国轮船上,行李包被小偷(其中有虾球)偷走,万贯资财尽失,年轻时即下南洋“卖猪仔”的此老人,一遍遍冲天悲号:“16年的血汗呀!……”
离开两个月了,不知老宋获得加拿大谈话否?真心祝愿他能够早日到达枫叶之国,忘记过去,安享晚年。
成稿于2010年4月1日星期四中午于曼谷寓所
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392
关于我们
本刊将秉持理性、平实的方针,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民众的维权活动,对社会焦点问题进行分析评论;同时普及宣扬人权理念,系统介绍国际人权法律知识和维权案例,推动法制建设,扩大公民社会的空间,为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服务。
过往各期
六四专题
搜索
热门转载

-
时事大家谈:赞“一士之谔”,中纪委反击中宣部?
-
小品:讨伐任大炮
-
魏京生: 任志強很勇 如同自己當年
-
任志强: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式分析
-
微自由: 任志强微博被封
-
《大炮有约》01 尼玛开撸,戴上头套谁敢惹咱俩
-
《大炮有约》任志强:不怕向任何人开炮
-
【中国情报】肃清微博大V | 中国走向法西斯二次文革? 20160301
-
批习「媒体姓党」遭清算 任志强微博被封 学者:已到二次文革边缘
-
党媒批任志强暴露党群对立

-
国土国家在茅于轼手里吗?
-
12国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
-
12国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
-
12国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