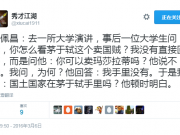敬告读者
为更有效地使用资源,《中国人权双周刊》从第181期起并入中国人权主网页。网址是:http://www.hrichina.org/chs。我们将继续遵照本刊宗旨和编辑方针,一如既往地为读者服务。
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透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下)
——中国威权资本主义下的政经利益犯
(接上期)
维权网2008年2月发表的“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指出:中国官方在1997年修改刑法时废止了“反革命”罪,以“颠覆国家政权”等危害国家安全罪取而代之。“当时,许多评论家对这一将刑法制度从政治中脱离的改革作了正面评价。但是,后来的经验证实这种脱离并没有兑现。各种国家安全罪仍然经常被用来惩罚行使中国宪法和国际人权法保障的表达自由的公民。”这是中国“换汤不换药”的恶法状况。
该文进一步指出:“关注中国人权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对话基金会认为,2006年被控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人数比2005年增加了许多。对话基金会的报告指出,其人数2006年是2005年的一倍。”
我们需要了解:这样一种“换汤不换药”,甚至“更加扩张”的恶法,究竟其背后的动力为何?有没有什么根本上的改变?
关注法律背后的社会关系
今年6月我和友人到香港参访时,和一个深圳青年谈了许久。他跟我抱怨了不少中国的政治状况、并且忧心忡忡地表示:“中国目前的社会,实在是太不公平了!”然而,当讨论到该如何可能改变这样的状况时,他却始终无奈地说:“实在很难,没有办法”,“在中国只要踏过红线,碰到敏感议题,政府一定会来阻止你”。这让我真实地感受到,中国威权镇压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如此之大,普遍地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痕迹:挑战政府的事碰不得。而能造就这样的效应,“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实行,有着关键的影响。
英国兰开司特大学(University of Lancaster)社会系教授Bob Jessop长年研究国家机器,他强调要将法律和国家当作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展现。也就是说,不将法律和国家给予本质化,赋予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角色,而是要将与其连结的社会关系一并观察,才能够清楚理解它们的内涵与逻辑。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抽象,但套用到中国“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看,会有新的启发。
过去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恶法的批判,多数是依循着该法的内容与逻辑进行,例如指出其作为一项刑法,相关的“构成要件”是否合理。当然,这往往也是一种相对“安全”的策略:就法论法,似乎能减少中共政权的封杀。然而,Jessop的理论提醒:我们要关注的不只是这些罪名的内容和逻辑,而是要一并将其延伸,来探索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为何,因为,这背后的“社会关系”,才是维持恶法的基础所在,或者甚至可以说,所谓的“恶法”本身就可以视为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种由国家机器所运行的“政策”。通过国家与社会双边互动而构成法律的观点,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分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恶法是中国国家和社会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所采取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理“策略”。
恶法实践透露的中国威权资本主义
循着这样的思考路径,我们在关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时,需要同时批判中国目前实行的政治经济模式———“威权资本主义”。是这样的政治经济模式,支持创造这样的法律罪名当作政治工具,来镇压公民的人权。恶法和政经体制两者,在设置上和实践上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以中国政府现在大力推动的“和谐社会”、“维稳”为例。我们在上回已经谈到诸多例子,中国政府为了追求“和谐”“稳定”,不惜大力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镇压社会中的异议者和反抗者。然而,要注意,这样的镇压和控制,越来越有着“选择性”:政府不只是憎恨那些散播反政府言论的人,他们更憎恨那些干扰“威权资本主义”运行、戳破官商勾结、断其财路的人。
对付这些侵犯到他们利益的异议者,政府采取的手段甚至不是公开地在法院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处罚,有时甚至暗中勾结黑道,把反抗者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理”掉。自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这在各地方政府的暴政中,特别能够看到。为了要维护招来厂商的黑金暴利,各种镇压人民的黑白手段,地方父母官都干得出来,其中许多以法律名义将人入罪。所谓的维护“和谐社会”,也就是要维护能让统治阶级获益的“威权资本主义”。
从“政治思想犯”到“政经利益犯”
进一步说,通过历史性地分析我们将能发现,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前,过去的“反革命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是属于中国“威权社会主义”的产物,其主要针对的对象,是被中共政权认为不合乎社会主义的异议者。这是传统意义下的“政治思想犯”,政府镇压思想上的异议者,维护社会主义思想和体制。
然而到了1997年,经历了十余年“改革开放”之后,“反革命罪”及“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替换为“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表面上,前后两个罪刑都是缺乏明确标准、任意罗织政治罪名的恶法,然而究其背后所代表的社会力与社会关系,却有着关键区别。在实践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已经不是真正用以处置“反革命”、实行“社会主义”的刑罚,而是成为中共当前“威权资本主义”的打手,维护的是官商具体的政经利益。
这前后两者罪刑的差别在哪?最大的差别在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镇压异议者的力量,已经不只是中共官方而已,而更包括了“资本”的力量,以及一连串地方官僚与资本勾结形成的“政经复合体”。过去,顶多只有得罪官方的异议者,可能遭受刑罚处置;然而在今日,不只是得罪官方,连得罪和官方关系密切的大资方,也可能因为意见不同而锒铛入狱。处置的对象,从过去单纯的“政治思想犯”,延伸到成为今日的“政经利益犯”。整体来说,控制的范围更是广大,而控制的目标,更是超出了过去的“政治计划”,而成了促进“资本不断积累”的禁脔。
因此,不只是要“颠覆政权”的“革命分子”可能遭遇不测,在这个年代,只要是影响资本利益的各种劳工权益、环境权益的“维权分子”,或“工运分子”、“农运分子”都可能是中国“颠覆国家政权罪”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要处置的对象。又或者,官方对于威胁较轻的民间活动,也会在祭出刑法之外,采取其它阻挠措施,这使得仅仅是要“扶贫”等民间组织也不得发展,只因为其在活动中随时可能触犯权贵的利益,一不小心就成了“政经利益犯”。
扶贫沦为政经利益犯的实例
举例而言,就在今年的2月,享誉国际、积极投入消灭贫穷工作的“乐施会”(Oxfam),其香港分部举办的青年活动,也遭中共教育部党组的公开封杀。
当时中国官方发出一份《防止香港乐施会招聘大学志愿者》的紧急通知到各大学,指称:“香港乐施会属于竭力向我内地渗透的非政府组织,且其负责人是反对派骨干。鉴于我教育系统特别是高校的特殊性,要断绝与其任何来往,不与其有任何形式的合作。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要统一思想,提高警惕,认识到香港乐施会招聘我大学生志愿者的用心不善,切实做好防范工作。”在强而有力、一条鞭的党务系统下,中国官方也的确成功阻挠了中国青年向香港乐施会学习扶贫工作的可能。
消息传出,民间维权人士纷纷大叹不可思议,因为长期以来,香港乐施会在中国的相关活动,就是走着“不批评中国政府”、“不直接介入维权活动”的“温和NGO路线”。然而,连温和的香港乐施会,要办个“实习青年招募”,都招来中共政权如此打压,更别提其它更深入的社运组织要如何发展了。
一个合理的结论是:问题已经不是运动人士态度温和与否、批不批评党,而是只要从事的活动凸显了当前中国政经体制的矛盾所在——威权资本主义下的阶级压迫——就成了必须要被镇压的对象。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标榜“温和”的维权组织或维权人士,同样遭到了中共官方的封杀,因为他们的活动,触及了这个体制继续运行的利益。
虽然目前遭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危害国家安全罪镇压的人士,依然不少是传统上的“政治思想犯”,然而也有了倾斜的轨迹,越来越多的触及到资本利益的“政经利益犯”,成为中国官方选择性镇压的对象。我们需要正视这样变迁背后代表的意义,才能理解诸多国家安全罪实践上的动力轨迹为何。
中国威权资本主义镇压异议者的三个动力轨迹
我们可以试着指出中国威权资本主义镇压“政经利益犯”,至少存在着三个动力轨迹。
第一、中国政权对异议者的镇压活动,日益受到资本利益的影响。如前所述,过去实施“威权社会主义”模式的中国,其政治控制主要是为了政权自身的稳定,以及有意推行的思想和实践。然而在“威权资本主义”的今日,中国政权不只得为了自身利益进行政治控制,还得为资本利益服务,以让此政经体制得以继续运作。例如,当前中国政权对各种罢工、工会、劳资冲突的介入,甚至对于带头工运分子的镇压,都反映着这样的轨迹:不只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有问题”,而是他们妨碍到了具体的“政经利益”,特别是资本的利益。
第二、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采取了一种“地方相互竞争”的模式,让各个地方政府为了发展自身的政经利益,努力站在资本的角度与其结合,甚至不惜牺牲任何人民的利益。如同我们观察到的,中国当前的各个地方政府,已经成为中央政府之外,镇压异议者最大的原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背后反映了,不论是来自法律或是事实上的政治镇压,都和“政经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地方相互竞争”的模式之下,地方政府甚至可能有着带头镇压异议者的主要动力。
第三、资本主义内部的经济危机规律,使得采取威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中国政权,必须在危机来临时,采取更加严厉、更加细微的政治控制手段,来弭平将使危机更加剧烈的任何挑战者。我们可以发现,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内部的各种阶级冲突已经越来越明显,而也正是在此时,中国官方对各种异议者的镇压,有着越演越烈的趋势。尽管有时表面上是以疏通的方式呈现,但都反映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共政权,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限制,而资本主义内在的危机问题,不但迫使中共采取各式各样的政治控制,甚至也预言了下一波中国巨大政经危机或变革的来到。
这些对镇压动力轨迹的分析,也是期望提醒当代的中国异议者:在对抗“中共政权”之外,“资本”也必然会是异议者需要对抗的对象。唯有将两者共同纳入分析,透视基于他们利益轨迹而来的种种镇压,才能理解我们为何被镇压,恶法为谁而服务。
总结来说,要透视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罪背后所显现的压迫来源,单单靠“去政治经济分析的自由主义人权论述”,是不足够的。我们必须要结合批判性的政经分析,指出那一整套支持、运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背后黑手,予以痛击。特别是需要提醒到:不能天真地认为,中国拥抱了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国人民的人权就会到来;恰恰相反,在资本主义的获利需求以及其和威权中国的结合下,中国成为了世界的生产工厂,为了利润,为了政商勾结,中国人民的人权更是如同风中残烛,随时有被侵害的可能。
结语:期许广大的人权关注
有意拿起镇压工具的统治力量,越来越复杂;然而,被镇压的人民一端,将会如何面对?
我的朋友告诉我,中国政府现在对付维权运动,有三大准则:“去串连、去领导、去多数”,通过这些控制手法,来让所有的维权运动成为孤立的少数事件。这不但维护了中国政权的稳定,也使得当前的“世界工厂”,能继续运行不坠。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控制手法是怎么奏效的?不是因为那些维权行动者真的被断绝了联系,成为个别的行动者,而是因为多数的中国人民,不但没有投入行动支持,反而冷眼旁观,甚至是成为支持镇压的意见帮凶。自然而然,维权也只能是个别事件,无法成为政治运动。
然而,当政治运动成为维权行动者的个人抵抗时,这样的政治运动还有可能维系吗?基本上是困难的。当那些“烈士”成为孤单的个人,他们的家人只能隐蔽在阴暗的角落中,不但没获得肯定,甚至是连安全都难以确保,这样的环境,又怎么能说服新一代的行动者要为理念牺牲,当那只扑火的飞蛾呢?更何况,如今我们要面对的敌人,恐怕已经不只是一个“政党”或“政权”而已,而是权力和资本交错的一套威权资本主义政经体制。
面对当代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体制,我们有充足支持变革的声音吗?我们要问:我们新一代的中国朋友,真诚关心自身以外,整体政治经济要变革吗?如果是,我们不该让这些受难者成为个别被噤声的烈士;星火燎原需要广大的要求改革的力量支持。在下一次镇压到来之前,让我们牵起手,一起在认识问题的过程中,看清楚压迫来源的轨迹,缓缓地向前迈进。倘若我们都看到,那条“红线”有踏过去的必要,与其是让烈士悲剧一再上演,不如更多人一起走过去吧!
注:作者为英国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社会学博士生
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572
关于我们
本刊将秉持理性、平实的方针,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民众的维权活动,对社会焦点问题进行分析评论;同时普及宣扬人权理念,系统介绍国际人权法律知识和维权案例,推动法制建设,扩大公民社会的空间,为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服务。
过往各期
六四专题
搜索
热门转载

-
时事大家谈:赞“一士之谔”,中纪委反击中宣部?
-
小品:讨伐任大炮
-
魏京生: 任志強很勇 如同自己當年
-
任志强: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式分析
-
微自由: 任志强微博被封
-
《大炮有约》01 尼玛开撸,戴上头套谁敢惹咱俩
-
《大炮有约》任志强:不怕向任何人开炮
-
【中国情报】肃清微博大V | 中国走向法西斯二次文革? 20160301
-
批习「媒体姓党」遭清算 任志强微博被封 学者:已到二次文革边缘
-
党媒批任志强暴露党群对立

-
国土国家在茅于轼手里吗?
-
12国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
-
12国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
-
12国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