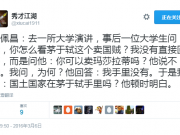敬告读者
为更有效地使用资源,《中国人权双周刊》从第181期起并入中国人权主网页。网址是:http://www.hrichina.org/chs。我们将继续遵照本刊宗旨和编辑方针,一如既往地为读者服务。
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冤化的地主
——颜恩统采访记
受访人:颜恩统,忠县花桥镇鱼箭7社农民,80岁
采访时间:2006年5月4日
地点:忠县花桥镇鱼箭7社
采访前记
去寻访颜恩统老人时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下起大雨,我们踏过一段弯弯曲曲的泥泞田埂来到老人门前时,身上已经被雨水浸湿了,这使得我们的心情一开始就非常阴冷。
80岁的颜恩统老人住在一间破败阴暗的土墙房子里,同妻子默默无语地“守候”着生命的最后残光。老人受过良好教育,容颜虽苍老,但眉宇间不乏儒雅之气。
我们两个陌生人的突然造访,让他有些意外,但话题转到土改上时,他却马上一五一十地说了起来,那样子好像是原先预约了的。看来,五十多年前的往事,虽然没地方倾吐,却没有一天忘记过。
老人是受过旧式教育的文化人,文化曾经给他带来无尽的苦难,但是也使他具有超脱的精神境界,他说:对付苦难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当人家在侮辱你时,你千万不要把他的话当真;你要当真了就只有去死,有不少人正是这样死去的。你自己清楚自己是什么人,他们怎么说是他们的事,别管他。他们只能伤害你的肉体,而不能改变你的精神。
老人向我们讲述往事时,他苍老的妻子一直默默不语地坐在旁边。那是一个受尽了侮辱与损害的可怜的老太婆,由于多年的折磨,她的神经已经近乎痴呆,双手已经拘挛,每天穿脱衣服都要颜恩统老人代劳。颜恩统老人说,妻子都是为他才受了这么多苦,所以他一定要好好照顾妻子,直到生命的终结。
正文
我今年80岁,是忠县县立中学四班的学生,毕业于1942年。县立中学就是现在的忠州中学。中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那时叫显周乡,当时在乡里我算是文化比较高的,所以老乡们就推选我当了保长,那年我才16岁。要是知道后来会发生那么多可怕的事情,我是绝不会去当这个保长的。其实当保长的时间很短,没多久我就去乡中心学校当老师了。
我一家四口人,父亲颜洪星,母亲王氏,没有名字,我有一个哥哥,抗战时上战场打日本人,去了就没有回来,死在前线了,这样我就成了独子。
我们家田产不多,只有300丈,折合不到3石粮,其中自耕一半多,出租不到一半。为什么出租?哥哥死在前线,我又在教书,家里缺少劳动力,就出租了一部分给人家种。土改时评成分硬是把我们评成地主,活天冤枉啊!按照当时共产党的政策,要25石租才可以评地主,我家就算全部出租也不到3石,怎么是地主呢?但是哪个让你申辩?他们想怎样整就怎样整,说什么就是什么。只要有一个人说你是,没有另外的人反对就行了。我就是这样成了地主。当时工作队是西南工作团——从部队转业的,对政策搞不清楚,反正听群众的。想申辩?你敢!我常常在想,如果真正照共产党的政策办事,我们乡只有韩茂生一个人够地主资格,其余一个也不够,但是我们乡被评为地主的却太多了,枪毙的枪毙,判刑的判刑,管制的管制,连子孙都受尽了迫害。迫害了就迫害了,几十年都过去了,还不是算了。
我除了被评为地主外,由于16岁时当过保长,又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于1951年2月被逮捕,判刑5年,押送阿坝藏族自治州劳改,刑满后我留场劳动到1962年才回乡。土改时的那些恐怖场面真是不堪回首,提起就难过。
老龙3队王石泉和王万木父子二人同时在鱼箭滩河边被枪毙,我被押去“受教育”,其实就是陪杀场。王石泉的罪名是干恶霸,什么干恶霸,乱栽的。王万木最冤枉,被枪毙时只有19岁,好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哟,他的罪名是反革命。说来太荒唐,他连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都搞不清楚,一个山区的娃娃,哪儿都没去过,知道什么革命反革命?乡里的工作组把他关起来,问他是不是反革命,他以为“反革命”是个很光荣的名字,就满口答应是反革命。哪晓得这就要了他的命,等到他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时已经没办法了。拔山区的领导对他是不是反革命有些怀疑,派人送信到显周来,叫暂时不要枪毙他,送信的人走了20里山路赶到显周场,有些累了,就在场上歇了一会,烧一杆烟再赶去鱼箭滩刑场,就在慢慢吃完烟走出场口时,听到鱼箭滩上的枪响了,显周到鱼箭滩很近,如果不是那一杆烟,王万木就不会死。
那一次杀了七个人,是何世新主持的,除了王石泉和王万木父子二人还有王在新——乡长、陈俊峰(音)——在县府当过几天兵的,加了个兵痞的罪名。周定芬是解放前乡公所煮饭的炊事员,吴家场人,也杀了。当时枪毙人没有标准,你要喊冤,一句话就把你打回去:“群众还会把你冤枉了。”“群众”太可怕了!你要再不服吊起就打。不犟(不喊冤)还少受点皮肉之苦。
仁和村的颜桂轩土改时已经80高龄了。颜桂轩民国时在县政府当了30多年的科员,一生清正廉洁,没有买过田地,只有祖上传下的几石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劣迹。他写得一手好书法,经常在县城狮子坝一家裱褙铺帮人写字,人缘很好,人们见到他都友好地给他一支烟。他在城里谋职,家里无人种田,就租给别人种,就这样,土改时也被评为地主。由于他30多年都在城里,家乡实在找不到他什么“罪证”,就说他在城里每天吃人家的烟是严重的贪污,30年算下来就贪污了不少。80岁的老人,身体已经很衰弱了,还是要弄来反复斗。落雪的寒冷天气,把他拉来“坐水盆”——就是脱掉裤子按进冰冷的水盆里受冻受辱。每天没完没了的斗争,他那么大一把年纪的人,好痛苦哦。他妻子比他年龄小一些,还勉强能撑住,看见他每天那么受苦,妻子实在于心不忍,就在一天晚上和他大哭一场后,狠着心把他卡死在床上,好让他得到解脱,不再活受罪。放哨的民兵发现后赶紧堵住他的屁眼(农民认为人死时气往下落,堵住肛门就可以不落气),不要他落气,还想再斗他,但是他已经死了。死了好些,少受活罪,当时都是生不如死。
韩茂生是被枪毙的,他妻子何代群被民兵们在光天化日下脱光衣裤按在地上分开两腿,把一个“包谷球球”(脱粒后粗糙不堪的包谷棒棒)插进她的下身去反复捅反复转动,何代群当场昏死过去。这是人做的事吗?不忍听闻!男人枪毙了,家产没收了,还要做啥子嘛?她没有死,手被吊打整爪(残废)了。周武灿(周爪爪)也是被整爪的,捆的时间长了血脉不通,手怎么不爪呢。
拔山乡五星村是冉泽民主持斗争大会,把地主十多岁的女儿裤子扎紧,再把黄鳝放进下身去乱钻,哪个不怕?又扒光裤子,双腿分开站在两个马凳(木工用具)上,用火烧下身,还美其名曰“烧飞机洞”。惨无人道,简直惨无人道!地主的女儿还没成年,有什么罪要受这种惨无人道的摧残!这是人做的事吗!就是那个冉泽民搞的,他是八德乡人,当时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
我被捕后关在拔山区监狱,和我同一个牢房的有一个叫李光荣的人,他是县中三班学生,比我高一班,任八德乡小学校长。我看见他腋下有一个很大的伤口,已经溃烂化脓,脓血发出的恶臭我都能闻到。他每天疼痛难忍,当脓血流出时,他就拿碗去接,吓人啦,脓血多得用碗接。从来没有人给他哪怕一点点药,他只有听任伤口溃烂。他的罪名也是反革命,这事也非常荒唐。土改高潮时,一个积极分子在他家墙外听见他和妻子商量:“是绑起来杀?还是不绑就杀?”积极分子据此认定他要杀民兵,就把他划定为反革命关了起来。而事实的真相是,他和妻子是在商量杀鸡,他是个知识分子,不会杀鸡,想绑起来再杀可能容易些。事后李光荣百般申辩都毫无用处,那些人对他进行了残酷斗争,李光荣腋下的伤口就是在批斗会上被他们打的。李光荣居然活了下来,现在还健在。
那时给地主喂狗屎、喂尿是常事。张仁强(显周医院退休医生)给我讲过,他的一个亲戚,是黄埔军校毕业的,给他喂狗屎,他规规矩矩地吃了,做什么都忍受了,最后还是把他枪毙了。
我去劳改后,父母没了儿子、妻子没了丈夫,他们在家受尽了折磨!莫提我父亲,不能提,提起我就痛心……父亲一辈子什么坏事都没做过,也没当过保长甲长之类,他一辈子就是种田。因为我的关系,1957年反右运动时,他被活活毒打致死。反右运动是在城市里针对知识分子展开的,我父亲是一个偏僻山区的农民,按理说无论如何也不是斗争的对象,但是,自从解放以来,我家乡历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规矩,就是不论怎么总得找几个人来斗争才算有成绩。找什么人呢,当然是地主啰,所以我父亲每次运动不管怎么都难逃劫难,反正说他不老实,“老实”已经没有界限了。
反右那年的八月初三,是令我伤心一辈子的日子,那天我父亲和妻子同时被拉到大河坝去斗争,就在鱼箭滩上面的一个竹林旁。所谓斗争只不过是一个政治术语,其真正的内容就是毒打,每次如此。你问是哪个动手打的?群众啊!是的,“群众”两个字太可怕了。负责主持斗争大会的是村党支部副书记颜光普,我本来是他的恩人,他被拉壮丁,跑到我家来躲,我当时是保长,他们家的人给他送饭,我说:“送啥子饭嘛,和我们一起吃就是。”就这样他才逃脱了拉壮丁。我怎么不是他的恩人呢?要知道,我亲哥哥都是拉壮丁出去死在抗日前线的呀。谁知道“解放”后颜光普翻脸不认人,讲起阶级关系来,把我往死里整。他对打手们放口说:“年轻的还要干活,颜洪星那个老家伙留着也没什么用了。”意思就是要打死我父亲。打手们得到了书记的指示,打起来就毫无顾忌了,木棒柴块一起乱打,又没有任何人说打错了,我父亲被打得满地滚,后来连滚都滚不动了。颜光普看见我父亲已经差不多了,才叫我妻子去挽起来。我妻子挽着父亲往回走,才走出十几步,父亲说要喝水,水还没喝完就一头栽下去,再也没起来。父亲的尸体草草地埋在鱼箭滩河边,没多久就被山水冲得不见踪影。
母亲和我妻子在一起艰难度日,苦不堪言。她们白天劳累,晚上民兵随时都可以来查哨,让你无法睡觉。那时到了秋收好不容易有了点救命的粮食,贫下中农们可以随时冲到我们家来把粮食抢走,就因为我们是地主。真不知那是什么世道。三年大饥荒时,母亲和妻子在家什么野菜都吃,连稻草都磨烂了吃,母亲还是没熬过来,饿死了。
我是1962年从劳改队回来才知道父亲和母亲惨死的经过,我去找父亲的墓地,已经白茫茫一片什么也没有了,我放声痛哭,我对不起父亲,身为独子,却连他的尸骨都找不到了。可是,除了痛哭,我还能做什么?我仍然是一个被管制的地主加历史反革命,人们依然可以随时斗争我。
听到妻子说起我去劳改后家里十多年来的苦难,我真的庆幸我去劳改了,如果我没去劳改,在家不被打死也要被饿死,总之绝对活不出来,我真的万分感谢劳改队,是劳改队救了我。和家中那些地狱般的日子相比,劳改队简直就是天堂。我摸着心窝子说句大实话,在劳改队的10多年,是我解放后最幸福的日子。
附带讲讲劳改队的故事吧。我们先是在重庆北碚劳动,后来远走阿坝州去修成阿公路,我们修的路段在著名的鹧鸪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飞雪,自然条件非常恶劣。那条公路可能是五十年代我国修筑的最艰难的公路,其艰苦程度难以形容。但是,我却很高兴,第一是吃得饱,还有牦牛肉吃;第二是每年都要发冬夏衣服,冬天的棉衣很暖和。就这两点,在家里是绝对没有的。更重要的是,只要好好劳动遵规守纪,就没有人来斗争你,这就少了许多恐怖。劳改队的指导员是四川达县人(今达川市),叫张文强(音),那真是个好人。他平常对我们很和气,从来不对我们耍威风,时间长了彼此熟悉了,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有时还大胆说些真心话。他总是很善良地提醒我们:“这些话跟我说没关系,千万不要去对另外的干部说,说了要惹麻烦哟!”他工资不算低,但是却不给家里寄钱,说家里钱多了不好,要穷才光荣。我们缺钱时,他总是主动借钱给我们。我现在都记得,他把手摊开,叫我们自己拿钱,一元两元随便,等有了钱再还他。那时一元钱是很值钱的哟。犯人家里寄钱来都要先由他审查,他从来不趁审查的时候先扣回所借的钱,而是把钱如数交给犯人。犯人去给他还钱时,他却从来不收,一律免了,说:“我不缺钱,你们的钱来得不容易,自己用就是。”这种人要不是我亲眼见了,还真不相信。通过他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论在多么残暴的年代,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依然会在一些人身上表现出来。后来,张文强调走了,他离开时,我们所有的劳改犯都流了泪。劳改犯都是些经历过大悲大痛心如死灰绝不轻易流泪的特殊人群,为什么会一起流泪呢?就是他太令我们感动了,直到现在,我还记着他的恩情。
我老了,身体又不好,我已经预先写好了自己的悼词。我讨厌现在的风气,不论生前做了多少坏事的人,悼词都把他说得很好,从来不说坏。我的悼词把自己的罪过也写了进去,我是有罪的人。我的罪不是别的,就是对不起我的父亲——他生前我没有尽到孝道,他死后我没有保护好他的尸骨。我有罪呀。
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881
关于我们
本刊将秉持理性、平实的方针,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民众的维权活动,对社会焦点问题进行分析评论;同时普及宣扬人权理念,系统介绍国际人权法律知识和维权案例,推动法制建设,扩大公民社会的空间,为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服务。
过往各期
六四专题
搜索
热门转载

-
时事大家谈:赞“一士之谔”,中纪委反击中宣部?
-
小品:讨伐任大炮
-
魏京生: 任志強很勇 如同自己當年
-
任志强: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式分析
-
微自由: 任志强微博被封
-
《大炮有约》01 尼玛开撸,戴上头套谁敢惹咱俩
-
《大炮有约》任志强:不怕向任何人开炮
-
【中国情报】肃清微博大V | 中国走向法西斯二次文革? 20160301
-
批习「媒体姓党」遭清算 任志强微博被封 学者:已到二次文革边缘
-
党媒批任志强暴露党群对立

-
国土国家在茅于轼手里吗?
-
12国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
-
12国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
-
12国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
-
“国际妇女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709大抓捕”中的女性》汇编文集